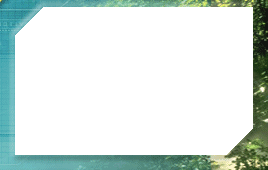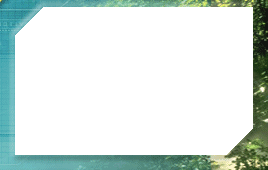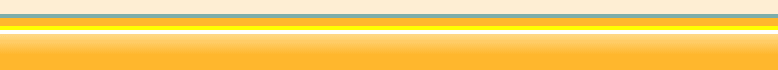最近一个时期,上至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下至最普通的黎民百姓,都在关注“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安徽凤阳小岗村年仅45岁的省财政厅下派干部沈浩同志突然猝死的悲剧。而我更多关注和思考的是大别山深处一个不知名的小镇——河南省新县沙窝镇最近两年接连发生4起青年村支书离奇死亡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上世纪90年代,我曾经在沙窝镇连续担任10年党委书记,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永久记忆和割舍不断的留恋之情。但在我离开8年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个个噩耗:先是我的继任者(当时县委调另一个镇党委书记来补缺,随后又调任县计生委主任),于2008年2月27日凌晨因饮酒过度猝死在跟县政府办公大楼一墙之隔的“金鑫娱乐城”(祥情见2008年3月11日《东方今报》记者余超报道:“河南新县计生委主任应酬饮酒过度猝死受表彰”),被媒体曝光后引发广大网民热议,炒得沸沸扬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紧接着,沙窝街道居委会和吴湾村二位40出头的青年村支书突发疾病不治身亡。当年年底,王山村党支部书记在镇里参加年终工作总结会聚餐饮酒后,在当晚返回家的路途中遭遇车祸就地死亡。2009年10月24日下午,沙坪村党支部书记在本村调解一起民事纠纷时,被街道上赶来滋事和行凶的5个青年农民持刀群殴致重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结果造成兄弟三人1死2伤的家庭悲剧。(祥情见2009年11月6日《大河报》记者报道:“河南新县一村支书被人在村口殴打刀砍致死,3000村民愤恨指控凶手”)此外,该镇还有一位离职村支书外出打工时遭遇车祸,落下一身残疾,至今仍卧床不起,需要家人全天伺候。
我初次与这5位村支书相识时,他们的年龄与我一样,都是20多岁生龙活虎的年轻人。上世纪90年代,我们在一起合作共事10年,共同度过了农村基层工作任务最繁重、社会矛盾最多、精神压力最大的艰难岁月,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和友谊。但如今,他们正值如日中天的黄金年龄怎么会“说没就没,说残就残废”了呢?今年11月初,我带领家人和5000元现金踏上返乡之路,怀着极度悲伤的沉重心情逐一走访和看望了这5个遭遇不幸残缺不全的家庭,其中一位村支书的女儿因遭受打击过重而落下精神分裂症至今尚未痊愈。当我看到4位英年早逝的村支书撇下他们年轻的妻子和未成年子女悲伤、凄楚、无助的眼神时,内心就像针刺和刀剜一样疼痛。因此,我从乡下返回城里的一个多月,几乎没有睡成一个囫囵觉。每当夜深人静时,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已故4位村支书往日不停地忙碌的身影,耳边甚至还能隐约地听到他们的爽朗笑声。在2010年的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我多么祈望还能像往常一样,和他们互相道一声问候——“请多多保重,岁岁平安!”
逝者已矣,不能复活。但作为生者,令我顿生疑惑和纳闷不解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农村基层工作环境可谓“糟糕透顶”——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六四”政治风波后,曾一度出现过农村改革10年“回头看”和集体经济“归大堆”的反常现象,导致农村改革初期连续出台5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历史使命暂时告一段落。随之而来的严峻形势是,城市规模扩张占用农村大片的良田,青壮年农业劳动力大批的外流,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相继撤出设在农村地区众多分散的营业网点,而当农村发展所必需的土地、劳力、资金等三大主要生产要素统统被抽走的时候,就算9亿农民有志气、有天大的本事也没用。特别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后,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只占全国的21%,而财政供养人员却占到了全国的71%,以至造成大多数乡镇基本处于一种“有政无财”的尴尬境地。当时,全国几百万名乡村基层干部长年累月的中心工作就是向农民群众伸手“要钱”(征收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屠宰税)、“要粮”(收取“三项提留”、“五项统筹”)、“要命”(抓计划生育、刮宫流产)、“要人”(组织农民群众义务投工修公路、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此外还要应付上级名目繁多的“升级达标”评比活动等等,他们从年头忙碌到年尾所付出的一切辛劳和汗水都属于“出力不讨好”和“净得罪人”的活。然而,即使在那样一个“大环境适应不良症”的非常特殊时期,人们也很少听到全国有哪一个地方的乡村干部被农民群众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致死的奇闻。倒是现在,全部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工作环境逐渐变得比从前宽松多了,平稳多了,容易多了,相反却在一些地方接连发生农民暴力抗争的群体性事件,以至让不少乡村基层干部患上了“自杀性传染病”。这种违反常理的恶性事件背后究竟隐藏着何种秘密和行为逻辑呢?
经过反复琢磨和深入思考,我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当乡村基层干部向农民群众伸手“要钱”的时候,通常扮演一种“双重角色”——既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代理人”,又是全体村民的“当家人”。他们作为“代理人”往往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而当他们作为“当家人”行事时又必须妥善处理“索取”与“回报”的关系,在二者之间寻找到一个“均衡点”,使双方达成互相理解、互相体谅、互相支持、互相包容、最终和解的的效果,尽力做到“社会风险最小化”。这是长期从事农村实际工作的基层干部在夹缝中生存炼就的一套“真本领”和“高超领导艺术”。但在国家实行“分税制”和“分灶吃饭”的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下,乡镇一级政府必须承担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千斤重担。否则,一旦当乡镇、村与农民之间的利益链条发生断裂,乡镇机关干部、七所八站职工、中小学教师、离退休人员等等几百号人就会出现“断粮断炊”的现象,更不要说维持乡村基层政权正常的运转了。所以,那个时期的乡村基层干部白天黑夜都泡在农户家里做思想疏通工作,对各家各户的经济收支状况、生产生活困难、邻里矛盾纠纷和家庭内部情况等等都了如指掌。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乡村基层干部就好像懂得全科医术24小时值班的大夫——“白天上门诊,晚上出急诊,深夜再会诊”,一天到晚基本没有一点儿偷闲工夫,从年头忙到年尾也顾不上照料自己一家老小和几亩责任田。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受,经常以默默奉献、忍辱负重的扎实工作,舍小家、顾大家,共同支撑起党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执政根基,与共和国一起度过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极度短缺的特殊时期。正因为这样,尽管上世纪90年代全国层层级级、各行各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轻农、卡农、挤农、坑农、抑农”的倾向,以至造成“有些地区农村人口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但却没有爆发像中国历史上那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当时,虽然一些地方也曾发生过因个别乡村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而导致农民服毒、跳井、上吊的恶性案件,但就整体情况而言这种现象毕竟是极少数。从这个意义说,全国几百万名乡村基层干部是一支富有农村基层工作经验和战斗力的乡土精英群体, 是一支同样呼唤理解和需要关怀的弱势群体,也是一个亟待“去妖魔化”而渴望获得社会公正评价的庞大群体。
当然,这并不是说乡村基层干部每年都把主要精力放在“要钱”上,虽然这是一项最缠人、最耗时、最费力、最复杂的苦差事,但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千方百计发展乡镇企业,开发农业支柱产业,培植地方财源,主动帮助农民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上的难题,否则乡村基层政权组织长期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就值得怀疑了。譬如,沙窝镇在上世纪90年代组织15600个农业劳动力义务投工投劳,对过境的106国道13.5公里路段和省道南信叶公路9公里路段土路基进行扩宽改造,利用国家“以工代赈”补助资金完成22.5公里柏油路面的硬化工程。同时,全镇14个行政村实现了村村通公路、通光缆电话、通有线电视,7000多个农户实现了通电、通自来水。此外,沙窝镇利用地处豫鄂二省四个县市(湖北麻城、河南商城、光山、新县)结合部和国道106线与省道南信叶公路线(河南信阳至安徽叶集)交汇处的区位优势,采取“低成本开发、市场化运作”的办法,加快建设中心小城镇,搞活省际沿边地区的农副产品流通。
所谓“低成本开发”,是指为解决小城镇建设资金短缺的困难,主要利用沙窝镇区周围的河滩地和山坡地改造,低价购买农户的承包地,组织全镇劳动力义务投工搞“三通一平”,然后再以当地“市场价格”出售给建房户,盈余资金全部用于街道路面硬化和其他配套设施建设。从1992年6月到2001年12月,沙窝镇主要通过这种途径实施“移民下山,兴商富民”工程,共筹集小城镇建设资金上亿元(其中包括国家投资2800万元,加拿大华侨捐款100万元,乡镇企业投资800万元,民间融资7000万元,小城镇土地出让金1000万元),使镇区面积由原来0.5平方公里扩大到4平方公里,街道居民占全镇总人口40%左右,建成了“豫鄂皖商贸大世界”,并于2008元旦期间成功举办了“豫鄂皖三省边区第一届商品物资交流会”。
在举行边贸交流会开幕式的当天,方圆数百里的上千家个体工商户和20万群众云集沙窝镇,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农民日报、河南日报、 信阳日报等新闻机构分别派出记者到实地采访报道“三省农民赶大集”的盛况。中央电视台制作的专题片《千年古镇展新姿》在央视一套新闻联播节目和第四套国际频道、第七套农村频道相继播出后,这对全镇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给予极大的精神鼓舞。1995年,原中共信阳地委、行署确定沙窝镇为全区21个综合改革试点乡镇之一,1998年,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又确定沙窝镇为全省82个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之一。1999年,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授予沙窝镇“文明城镇”称号。2000年,河南省人民政府确定沙窝镇为全省115个重点建设镇之一。
沙窝镇当年之所以取得这样辉煌的建设成就,并让当地老百姓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分享到“看得见、摸得着”实惠,主要经验就是“让群众的事情自己做主,基层组织积极引导”。具体来说,一是“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队伍促发展”,如对镇机关干部实行竞争上岗聘任制,鼓励富余人员分流“下海”创办经济服务实体;对在职村干部实行结构效益工资制,对离职村干部实行养老补贴制度,建立健全村级后备人才库;对无职农民党员实行分组管理,建立党员联系户制度;对七所八站负责人实行季度工作汇报制度;建立健全村民议事会、红白喜事理事会、民事调解理事会、治安联防体系等等。通过这些改革举措,激发了全镇上千名党员干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活力,形成了上下左右配合、齐心协力“同唱一台戏”的农村基层工作新格局。二是坚持“在学中干,在干中学”,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阔视野,破除小农意识。在沙窝镇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我们每年组织全镇党员干部和部分街道居民分批到周边的叶集镇(安徽省重点建设镇)实地参观学习;当沙窝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后,我们每年组织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和14位村支书分批到江苏省华西村实地参观学习。同时,我们每年都要组织召开“千人动员大会”和各种类型的“座谈会”、“碰头会”、“经验交流会”,让镇、村、组三级干部、无职农民党员、乡村中小学教师、离退休人员、街道个体工商户、农村宗族领袖人物等等成为党委政府的“传话筒”和“播种机”。全镇党员干部几乎每天都与农民群众粘和在一起,有苦同吃,有难同担,进行“面对面”交流和思想疏导工作,及时消解部分老百姓心中的怨气和牢骚情绪,逐步形成一种“有张有弛、和谐有序”的农村基层工作运行机制。(祥见张新光著《乡镇基层政府是推进我国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对河南省新县沙窝镇10年决策过程的系统观察与思考》,原载《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10期)
当我离开沙窝镇时,对那个时期的乡村基层工作留下两点深刻记忆:一是,村干部平时只记得“农历”而不知道“公历”是何物,乡镇干部平时只记得“阳历”而不知道“周末”和“星期天”是何物,只有在县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二是,乡村农村基层干部长年从事百分之百的苦活、累活却只能得到10%的回报,而在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平时习惯于“一杯清茶、一盒烟,一张报纸看一天”的悠闲工作环境却可以得到高工资、高津贴、高福利。比如,从1992年6月到2001年12月,我在沙窝镇担任党委书记期间的月工资由102元(基本工资89元+工龄工资7元+下乡补助6元)提高到536元,将近10年时间才增加434元(由镇财政支付)。而当我2001年12月调任信阳市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后月工资从536元猛涨到1200元(由市财政支付),2002年1月正式转入信阳师范学院工作后月工资标准又从1200元翻倍增加到2400多元(由省财政支付)。为何同样一个国家公务员“屁股挪一挪窝”待遇竟然发生天壤之别呢?这难道是当今中国社会一种正常的政治经济秩序吗?
以上罗嗦讲述了那么多“陈年往事”,无非就是说明一个问题: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前,我国绝大多数的乡村基层干部“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但在农业税取消后却出现了“无人管事、无心干事、无钱办事”的怪现象,甚至一些地方正在出现“乡镇空巢化、村官行政化”的新苗头。所谓“乡镇空巢化”,是指乡镇机关工作人员和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办公经费全部改由中央和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解决后,使不少乡镇领导干部产生了待遇“旱涝保收”和工作“无事可管”的思想,他们在正常工作日乘坐专车“早出晚归”往来于县城和乡镇之间, 其他一般干部骑着摩托车上下班,几乎所有人都变成了“候鸟型”的走读干部。因此,乡镇基层政府机关现在一到“周末”和节假日期间经常上演“空城计”而出现“空挡”现象,原本在县级以上党政部门才存在的“机关病”开始向下转移和扩散。
所谓“村官行政化”,是指村两委干部经济补贴和办公经费全部纳入县级财政供给后,使不少村干部产生了“准政府官员”和“端谁的饭碗,给谁做事”的思想,他们在平时的工作中只听从上级指挥和使唤,不愿意接触群众而与农民失去了交流和联系。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一方面是久已存在的“村庄空心化”和“家庭空巢化”现象越来越普遍,一方面是正在出现的“乡镇空巢化”和“村官行政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我担心照此发展下去,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还能维持多久?我国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又将如何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那么,问题的症结究竟出在何处呢?我认为,这决不是一种乡村基层干部工作作风蜕化的“慢性病”,而是我国在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相关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而存在“政策漏洞”造成的结果。
——从1999年到2005年,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总体进程是由“减轻、规范、稳定”的过渡性目标转向最终取消农业税。在这一时期,中央和省级地方财政转移支付重点是保障乡镇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和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兑现,而没有考虑如何解决离退职村干部、农民无职老党员和村民小组长的待遇问题。这样就使原本已经享受村集体经济补贴的人在资金筹集渠道上出现了“断流”和“空挡”的现象。因为,这部分人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前享受经济补贴的筹资渠道是“乡镇企业补一点、村级集体经济出一点、地方财政拨一点。” (参见中组部、人事部、财政部、民政部联合下发组通字[1992]15号文件《关于妥善解决离任村干部生活困难问题的通知》,1992年6月30日)但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过程中,农民除交纳7%的农业税和1.4%的农业税附加外,不再承担其他任何名目的“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乱集资”。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乡村基层干部对辛辛苦苦征收上来8.4%的农业税费自然会采取“近水楼前先得月”的优先支配权,而只得把离退职村干部、农民无职老党员和村民小组长“搁置不议”。特别是在农业税取消后,在职村干部的工资待遇和办公经费全部纳入县级财政预算解决,而离职村干部、农民无职老党员和村民小组长却变成了“没娘管的弃儿”。
于是,我国农村基层工作中长期形成的“统一战线”开始出现了裂痕和对立。比如,沙窝镇党委于1993年3月制定出台《关于离退职村干部享受经济补贴的若干规定》,对建国以来在“土改”、“四清”、“农业学大寨”、“大包干”等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参加农村集体工作、且长期坚守在基层工作第一线的离任村干部。根据他们任职时间长短和贡献大小,分别给予一次性补助或享受不同比例的定额补贴。这充分体现了上级党组织对离退职村干部的关怀和爱护,同时也充分调动了在职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维护了基层干部在农民群众中的威信,极大地推动了农村改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沙窝镇身体尚好、且有一定影响力的离任村干部都主动出来在村里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凡是在职村干部在群众工作中解决不了的难题,一般都是依靠老支书、老村长出面“说和、解套”。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在一些重大节日,经常组织慰问活动,认真听取离任村干部、农民无职老党员的意见和建议,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了一种尊重和关爱老干部、老党员的良好风尚。可以说,那个时期的在职村干部真正把离任村干部和农民无职老党员当作“宝贝疙瘩”看待,老支书、老村长、老党员利用过去的“余威”和在群众中留下的影响力而成为在职村干部工作上的“靠山”,他们在平时的工作中交往十分频繁,个人感情和私交也相当融洽。
然而,现在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和乡村干部与离任村干部和农民无职老党员几乎失去了一切联系和沟通,有的老支书、老村长、老党员甚至因为结伴越级集体上访而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就连他们过去亲手培养成长起来的“接班人”也把自己当作“仇人”看待,平时在村子里碰头时也不搭腔说话,在职村干部与离任村干部长期“内耗互斗”的最终结果是两败俱伤。当下,沙窝镇不少农民一提起某个村支书的名字,随口就会说:“村支书算个吊!”(当地老百姓骂人的脏话)。
在沙窝镇最典型的人物是陈高山村党支部原书记陈登峰,该同志在1950年搞“土改”时参加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村团支部书记、民兵营长、生产大队会计、副大队长、大队长等职。自1973年起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直到1998年冬季突发脑溢血病倒在农田水利建设工地,在农村基层工作第一线默默奉献了将近半个世纪。该同志担任陈高山村党支部书记期间,在全村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中享有“一呼百应”的崇高威望,是新县198个村党支部书记中的“一面旗帜”,曾经连续当选河南省第七届、第八届人大代表。1990年3月,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侯宗宾同志在大别山区视察工作时,主动提出专程到陈高山村旁听和体验陈登峰同志给农民党员上党课的场景。
就是这样一位经历资深、颇具威望、身份特殊的村支书,在1999年春季退休后,对照沙窝镇党委1993年制定的《关于离退职村干部享受经济补贴的若干规定》的条件和标准,也只享受到相当于在职村干部全年报酬60%的经济补贴,每年大约为1800元左右。但在2002年河南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后,该同志仅仅享受3年离职生活补贴,也毫不例外地宣布取消和终止了。如今,陈登峰同志一年至少要花去医疗费5000元以上,加上他和老伴二人正常的生活费用开支,平均每年起码需要上万元的经济来源。这对于一位年近80岁、且半身不遂的退休老人来说,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2006年开春后,他只好“变卖祖屋”作为本钱,和老伴一起搬进县城与小儿子一家人共同生活。
目前,在沙窝镇14个行政类似这样的离任村干部还有20多位,有的做小贩沿街叫卖,有的在山上放牛,有的打零工,有的捡破烂,有的投亲靠子女生活……这些长期辛勤操劳在农村基层工作第一线的离任村干部体弱多病,生活困顿,晚景凄凉,处境艰难, “走在村里抬不起头,站在人前没面子,回到家里尽受气,想找组织没人搭理”,他们往日留在农民群众中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威信已经荡然无存。总之,我国农业税取消后把上百万离任村干部和农民无职老党员长期“晾晒”起来,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哀和无奈,更是对党和国家长期以来培植的农村基层社会“政治代言人”和“政府代理人”形象的极大讽刺和精神损害。(祥见张新光著《着手解决村干部报酬的资金来源问题刻不容缓——河南新县沙窝镇几十位离退职村干部缘何在农村“费改税”后伤心流泪?》,原载《决策》2005年第3期)
——从2006年1月1日起至今,我国正式进入了所谓“后农业税时代”。 最近几年,我国进行农村综合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三项”(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和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构建“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乡镇基层政府,使其由过去的“管治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全国大多数省份主要基于减轻地方财政压力的考虑,热中于“撤乡并镇”、“合并村组”和“减人、减事、减支”,而对乡镇机构改革后如何保证其“高效运转”却迟迟没有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
同时,不少地方在推进乡镇机构改革的政治风暴中采取“无情改革、不得拖延、不留过渡期”的强硬措施,对乡镇临时借调和临时聘用人员实行“一律清退,不予补偿”的政策,对乡镇分流人员分别给予3000元~5000元不等的一次性补助,对“集中处理掉”的村干部不予补偿;而对于乡镇、村在编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和办公经费则由县级财政全额供给。这样就使“被排挤出局的人”与“挤进编制内的人”在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差。
特别是这次被清退掉的村干部过去承担税费征收任务重,付出劳动和汗水多,遭受责难和屈辱大,得到理解和回报少,但在离任后却背负一身的“三角债”(农户拖欠税费不交,村干部自己垫资完成乡镇任务,村集体再给离任村干部打白条),他们自然就成了在职村干部的新的“对立面”。比如,河南省在2005年下半年,仅用3个多月共撤并乡镇236个,合并各类事业站所3117个,精简乡镇领导职数接近三分之一,清退乡镇临时人员20551人,分流乡镇超编人员170022人,仅此一项平均每年可为省级地方财政支出减少20亿元左右(当年的农业税取消后,乡村基层组织缺口资金29亿元,除中央财政转移支付18个亿外,尚需省级地方财政自身消化10.8亿元)。
同时,全省统一规定:较大的行政村干部职数由原来的7~9人减为5人, 较大的行政村由原来的5~7人减为3人。 河南省在这次乡镇机构改革中虽然也强调“要把乡镇工作从过去直接办企业、抓生产经营、催收催种、收费罚款等繁琐事务中解脱出来,转向典型示范引导、提供政策服务、营造发展环境和维护社会稳定上来”, 但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和激励约束机制,现在的乡村干部竟然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祥见张新光著《地方政府变革的动力机制分析:对河南省三次乡镇机构改革的观察》,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该文曾被《新华文摘》2006年第23期转载)。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既是正确认识事物客观存在和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本规律,又是准确把握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性质和工作格局正在发生新情况、新变化、新趋势的辩证法。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提升到国家宏观层面来考虑,作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为核心,建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制度框架,掀开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篇章。
据不完全的统计,从2003年到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投入累计达到2.87万亿元,年均增长22.7%,其中直接用于农民“四项补贴”的资金累计达到3406亿元。目前,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体制由过去主要依靠农民自身解决转向以国家投入为主,全国约有1.5亿农村中小学生享受免费义务教育,8.15亿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4284万户农村困难群众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条件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党中央和国务院之所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调整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一方面想让9亿多农民“休养生息”,一方面试图缓解农村基层党群干群“高度紧张”的关系。
然而,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现实是“农村原有的基层组织体系网络破坏了,乡村基层干部队伍解散了,离任村干部和农民无职党员灰心丧气了”,乡镇政府变成“守摊型政府”,村干部退化成“跑腿型干部”,乡村基层政权已经演变成了“一座孤岛”。因为,所谓的“乡土经济精英”是指在农村改革初期先富裕起来并对当地经济发展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物,他们过去曾经为村庄经济发展寻找市场机遇、带领村民共同致富、为村庄公益事业出钱出物等等;而目前这些人早已离开生养他们的故土走向城市发展和居住,平时与乡亲往来稀少,几乎失去了一切联系。所谓的“乡土社会精英”是指一些农村文化人和宗族领袖人物,他们个人品德高尚,掌握一定的和文化知识和丰富的社会经验,在民间社会的公共领域里具有一定影响力,如主持村民各家的红白喜事、调解民事纠纷、充当民间交流的中介人等等;而目前这些人要么体弱多病,要么不受乡村基层组织重视,已经不再热中于村庄内部的琐事了。
所谓的“乡土政治精英”是指乡镇机关干部、七所八站职工、离退休人员、乡村中小学教师和村党支部成员、 村民委员会成员、村民小组长、村民理财小组成员、村民议事会代表以及共青团、妇女联合会、民兵等群众组织成员等等,他们一般都掌握或大或小的公共权力,在农村基层社区管理和群众生活中发挥领导、决策、组织、协调、整合的功能和作用; 而目前河南省在乡镇一级只剩下几十号人(按照全省统一规定:人口在4万人以下的乡镇,行政编制核定为24名,事业编制核定为40名;人口在4至5万人的乡镇,行政编制核定为27名,事业编制核定为43名;人口在5万人以上的乡镇,行政编制核定为30名,事业编制核定为46名),在村一级只剩下三五个人(全省4.7万个行政村已有83%实现了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单靠这些人去治理好中国庞大的农村社会可谓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比如,日前发生在河南省新县沙窝镇的一起人命案基本属于当地政府和县环保局“行政不作为”所导致的恶果。(祥见2009年11月13日《河南日报》记者尹海涛报道:“河南一村支书因污染纠纷遭殴致死矛盾由来已久。”)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取消农业税后,我国乡镇基层政府、村级集体组织与农民群众之间的利益链条中断,彼此互相牵制、互相约束、自动调节的均衡机制失灵了,而一旦失去约束的“公权力”怎能不发生蜕化变质呢?
(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