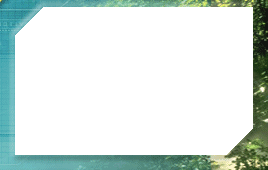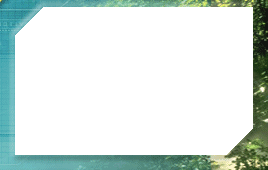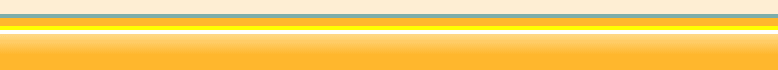浙江新文学作家群的崛起,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之一。浙江作家群体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突出之处首先在于阵容壮观,可载入新文学史册的作家就多至百余人。更为重要的是,许多作家还是现代文学思潮或文学创作的开创者、领衔者。
人文传统:地域背景中“人文因素”之重
浙江新文学作家群在“五四”以后的强势崛起与浙江特殊的地理区域类型和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从文化发展的走势看,如果更多地考虑“人文因素”的作用,对于近现代浙江士人更具感召力、产生更直接影响的,当是启蒙传统的现代延续。
浙江的启蒙文化思潮始自南宋。南宋定都临安(杭州),这里人文荟萃,又得东南雄厚财富之利,遂显一时文化繁荣之景观。宋明以来,浙江人才辈出、学派林立:由南宋开启的“浙东学派”,创事功学与心学两大体系,确立近代理性所需的务实精神和张扬人的精神主体性的哲学理念,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启蒙之先河;至明清之际,集心学之大成的王阳明哲学与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史学,促成了事功学与心学的合流,建构了一种兼具主体精神与事功精神的哲学理论体系,使这里成为当时新思想、新思潮的主要启蒙地区。在此“背景”下,后来走出一个以启蒙为重任的新文学作家群,可谓是历史传统的承续,是文化启蒙思潮蓄势已久的喷发。
浙江作家在审视文化、文学思潮时,往往对此地自宋、明以来颇盛的启蒙文化思潮表现出自觉的怀恋与认同。20世纪初,新一代浙江学人在日本东京创办了《浙江潮》,做出激昂的发问:“浙江省文明之中心点也,吾浙人果能担任其此言乎,抑将力不能胜任,徒为历史羞乎?” 这里所说的文明“中心点”,显然是指从南宋以来的两浙文化传统曾居于“文化中心”地位,表露出新一代浙江学人自觉追踪同乡先哲,油然而生的承传地域文化传统的自豪感和使命感。不妨说,带着一种对前贤造就的文化传统的自觉接受意识,应是许多浙江新文学作家紧紧抓住新世纪到来之机运,作一次开拓新文学努力的原动力之一。
文化的承传更多的是无形的、精神上的,因为一个地域积淀的历史文化传统总是以“集体记忆”的方式留传后世。考量浙江新文学作家群对两浙启蒙思潮在精神上的呼应,也许更能触及承传关系中的本源性问题。近代以来思想文化启蒙思潮所关注的最根本问题,是确立人的近现代理性,使人摆脱封建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束缚,获得个体精神的自由和人性的解放。在此,最能看出浙江新文学作家与他们前辈在精神上的相通。浙东学派所鼓吹的启蒙思想,便包含了针对长期以来经学统治造就的忽视人的现实存在和自身发展的弊端, 提出重新审视人的全新观念。而浙江新文学作家也正是在“人学”命题上作出了承续又超越前贤的探索。 周作人首创“人的文学”理论,在新文学建设中无异于炸响了春雷;茅盾、郁达夫等也从不同角度阐述过“人性解放”、“个人发现”是五四文学“主要目标”的意见;而鲁迅作为启蒙主义文学大师,早在新文学诞生前夜,就已在《文化偏至论》等文中提出系统的“人学”理论。在创作方面,尽管早期浙江作家对文学思潮、创作方法的选择有所不同,但都基于其自觉的启蒙意识,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自由平等、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等思想。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继承了两浙人文精神中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道统的反叛,其创作中的启蒙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启蒙精神的现代延续。
历史机运:“小传统”地域占得文化先机
新文学作家群在特定时期猝然爆发,还取决于独特的历史机运。费正清指出:中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着两个对立的传统,即“面海的中国”的“小传统”和“占支配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腹地”的“大传统”。前者表现为先进的“城市—海上的思想”,后者则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文化的传统制度和价值观念”。自近代海禁大开以来,“面海的”富有变革精神的“小传统”渐次获得生机,其释放的巨大能量日益改变着被“支配”的角色定位,而日渐由“边缘”向“中心”位移。浙江作为“面海的中国”的一部分,能在19、20世纪之交得风气之先,率先经受近代文明思潮的洗礼,便源于这一根基厚实而又敏于新变的文化土壤。
“小传统”地域之具有文化生机,在于“面海”的拓展性、开放性优势,它蕴涵着融通新潮、因时而进的改革气度,因此当中国有可能向近代化的方向迈进时,这里就会获得变革的先机。这个区域文化场地处海隅的流动性特征,赋予这里的人们一种乐于外向拓展、积极进取的文化性格。这种外向拓展意识,对于走出自我封闭,广纳异质文化,从而加厚加深自身的文化积累,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19、20世纪之交,值文化思潮大裂变、中西文化激烈冲撞之际,尤易使外向拓展的意识获得加倍张扬的机遇和可能。一方面,国门既开,为“面海”地域的人们率先提供了探头向外的条件;另一方面,异域新风的吹拂,也使他们首先感到勇迎世界之潮流实为当务之急。大量浙江人在当时跨出国门,留学生群体中走出了日后浙江新文学作家群中的中坚人物,成为构建五四新文学的中坚力量。
新型作家队伍的形成是建构新文学不可或缺的前提,那么文化新军的积聚对于改变近代以来作家队伍的整体结构,进而实现文学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产生了多方面的意义。首先,作家队伍知识结构的更新和意识观念的调整,奠定了向现代转型的底色基调。这新一代学人大都有“旧学”根基,又有“西学”背景。在现代化进程中,总能站在时代前沿,不断刷新文化思想、文学观念,到后来完成整体性的现代转换。其次,新一代学人在择取新知中重在对世界进步学问的深究,还表现出向文学一面的倾斜,这使日后的新文学受惠甚多。再次,这新一代学人还表现出对文化新潮的敏锐感知,在20世纪初已开始向文学的“现代”方向发起强有力的冲击。例如被郭沫若称为“一对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的鲁迅与王国维,在当时就表现出目光如炬的改革气度。他们在文化思想、文学观念上迥别于他们的前辈,明显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文体变革和创新:地域文化精神的驱动
严家炎说:“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文学天空群星灿烂,那么,浙江上空的星星特别多,特别明亮。” 在新文学开创期,不难看出浙江作家率先表现出文学观念的更新和新文体意识的觉醒,在新文学创作中作出别地作家无可比拟的成就。细察浙江新文学作家的创造精神,不难发现有两浙文化传统的驱动作用。
文体的变革、创新与时代精神是相切合的:适应新兴的社会思潮与文学思潮,旧有文学观念被颠覆,必促成文体意识的调整。五四新文学建设的一个突出表征是,文学“为人生”命题的强调和平民化趋势的加浓,传统的文体观有所改变,于表现人生有用、易于为平民所接受的文体形式不再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于是就出现了传统文体观念中“主要样式”(散文、词赋)与“次要样式”(小说、戏曲)畛域的打破,乃至造成后者由边缘向中心位移。针对小说与戏剧的“邪宗”说,钱玄同与此唱反调,他说,“小说戏剧,皆文学之正宗”,并认为“此亦至确不易之论”,于是把数千年的传统观念作了个空前的颠倒。沈雁冰在新文学开创期接手《小说月报》编务时,即提出“说部、剧本、诗,三者并包”的方针,其目的显然也在于提高小说与戏剧这两种“次要样式”的地位。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这两部文学史的辉煌巨著,一前一后呈现于20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坛,都在于提高小说与戏曲这两种“次要样式”的地位,他们在文体选择上的默契绝非偶然,而与拥有一个共同的区域文化场密切相关。
地域文化传统对文体变革的影响,既反映在对“次要”文体样式的提升上,也应表现在对传统“正宗”文体的现代转换上。事实上,素有“散文大国”、“诗歌大国”之称的中国诗文传统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被轻易抛弃。就文体的历史传承与现代延伸而言,散文应是最早彰显传承关系且取得显著实绩的文体。“五四”前后的时代潮流与晚明几近相同,“王纲解纽”的时代环境将现代知识分子推到历史前台,文学担负起“启蒙”与“救亡”的双重责任,因此适于推进“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散文文体也就有了独步文坛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相近的时代氛围中产生的散文文体的承传与革新,最能看出地域文化精神的承传关系。对古老散文文体的改造,浙江新文学作家亦多有建树:周作人创“美文”说,改变了传统小品文的观念,将其演绎为“诗与散文中间的桥”;鲁迅则向传统的文学观念挑战,将杂文列为文学“正宗”,并使之“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 这都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之举。散文文体的革新,显然受到“乡先贤”的启悟,正是此地晚明以来颇盛的文体革新之风促发了他们改革文体的思考。
在诗歌领域,新文学作家对这一积累深厚的传统文体的改造,是破除其繁杂形式,使之成为心口相随、自由表达的文体。其中的一个表征是由“文”向“白”、由“雅”到“俗”的转变,这恰与浙江作家的“平民文学”主张和“俗”文学追求谐和,于是就有了其在初期白话诗上的用力探索,周作人的《小河》、沈尹默的《三弦》等都是当时脍炙人口的名篇。联系到鲁迅、周作人对“乡土艺术”、“乡土文学”的重视,便可理出一条清晰的思路:深受地域传统文化的影响,新文学“浙军”继承前贤的文体革新精神,总是不断地为拓宽新文学的表现内涵而寻求变革之途,于是也便有了他们在新文学多个领域的广泛建树。
两浙文风:地域环境造就的文学风貌
浙江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吹刮的“江南风”,渗透着鲜明的地域色彩,在整个中国新文学中可谓独树一帜。最鲜亮的标记,无疑是浙江作家笔下浓墨渲染的吴越文化氛围和浙江山川风光,那是任何一个来自别地的作家之创作都无法混淆的。鲁迅小说中的“未庄”、“鲁镇”、“S城”,周作人散文里的“乌篷船”、“故乡的野菜”,茅盾笔下刻着杭嘉湖水乡印记的小镇、乡村,是那样深刻着“浙江”的“胎记”,任何力量也无法将之抹去。还有走到天边也改不掉的“乡音”,读刘大白的早期白话诗,一望而知这是用浙东的方言俗语写成的,浙江人读起来犹如异乡遇故知般的亲热。而作为深潜的“浙江”标记,则体现着两浙文化精神的浙江人的意识观念、思维方式、文化性格等,这些积淀在浙江作家意识深处的东西,总是在其笔端有意无意地表露出来。
考察历史形成的浙江作家的文风,还应有两浙之分。所谓两浙,是指以钱塘江为界,把浙江分隔成“浙东”、“浙西”两块。细分“两浙”,因区域性的生存形态(地理环境、物候气象、民俗风情、人文环境等)的不尽相同,便会产生质地很不相同的文化品性。浙东和浙西人的秉性就有较大差异,群山环抱的浙东之坚硬劲直(土性)与水网密布的浙西之温婉秀美(水性)形成鲜明对照。
体现浙西“水性”文化特色的作家之文风大都偏于秀婉,可以说属“飘逸”一路。浙西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并非都归属这一路,例如从杭州走出的夏衍,其创作就颇有刚毅之风。然而,浙西作为两浙“飘逸”文风集中显现之地,“飘逸”之风毕竟在更多的新文学作家身上得到了反映。典型的作家如来自杭嘉湖地区的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施蛰存等。
与此对照,浙东新文学作家文风的刚韧、劲直恰恰印证了素有“浙东硬气”之称的传统文化品格,从中可见它与浙西文风的极大差异。其文化性格中的“刚性”质素同传统浙东文人是一脉相承的,其艺术思维深至与厚重,文风该归于“深刻”一路。从浙东走出的作家,除周氏兄弟外,还有冯雪峰、艾青、柔石、巴人等,都显出坚硬的“土性”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这里走出的两个作家群体:一是浙东乡土作家群,包括许杰、许钦文、王鲁彦等,其创作师承鲁迅,演绎出土性十足的浙东坚硬民风与民气,形成以启蒙话语为主导的沉重坚实的创作主题,在“土性”的尽情挥写中透出“深刻”。二是浙东左翼作家群,包括柔石、殷夫、应修人、潘漠华等。这个群体的形成固然取决于该地当时浓厚的革命情势,但浙东刚烈民风营造坚硬性格、激扬文字,当是更内在的原因。看来,地域文化传统对许多作家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它一旦作为精神性的东西世代传承,总会以极强的渗透力浸染、塑造作家的文风,使其在创作中或隐或显地呈现出来。
浙江新文学作家群的生成,应是此地浓厚的启蒙文化传统的现代延续,也是作家敏锐感知文学新潮、把握历史机运的结果,这必然有助于推动浙江新文学作家的变革和创新,从而形成独特的文风。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