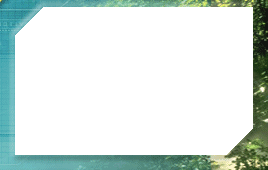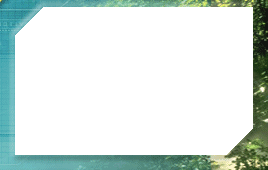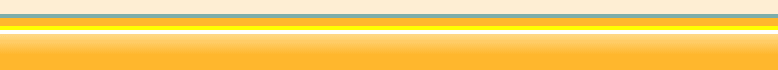引言
解放前我国农村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矛盾制约下, 逐渐出现了土地占有权逐渐分散、而使用权相对集中的趋向。由于高地租率的压力,土地使用权实际上只能向生产能力强的自耕农(亦即中农和富农)集中。因此,早在解放前土地产权即已经是“两权分离”了,这其实也是使资源配置相对合理从而稳定农业生产的重要的制度因素。小农的基本行为取向是尽可能多地租种土地,以“劳动替代资本”投入来增加剩余、从而稳定农业生产;但同时又会使人口随之不断增加,落入发展经济学指出的“增长陷阱”[2]。我们熟悉到,土地占有上的不平等不是农村贫困、小农破产的主要原因。
本篇的分析使我们进一步熟悉到摘要:旧中国发生农民革命的直接原因是农民贫困和农业破产,但从本质上看,最主要的原因是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对农村的过量剥夺。国家以工业化为目标必然会从农业提取剩余,然而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剩余太少且高度分散,和工业化目标相冲突。在工商业发展的拉动下农业商品率不断提高,为商业和金融资本进入农村经济打开了大门。而在这两种能够和地主经济结合的大资本过量榨取小农剩余的功能下,农村经济必然衰败。因此,真正造成农民贫困和农业破产的主要因素,其实是商业资本的“剪刀差”和金融资本的高利贷。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结构大幅度调整、商品率不断提高,农村高利贷多有发生,农产品国际贸易和国内流通的新问题也愈益复杂,这些都曾在本世纪初叶发生过。因此,探究中国发展新问题的人们有必要以史为鉴。无论今人采取什么途径追求现代化,都应记取工商业和金融资本剥夺农民导致农村衰败的历史教训。
一、农业种植结构的市场化
随着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进入中国形成的买办工业,以及洋务运动以后官僚资本和城市以轻纺、食品为主的民族工业兴起,中国农村种植结构不断调整,农产品商品率增加。黄宗智[3]曾经分析道摘要:“中国农业在19、20世纪,成为世界商品市场的一部分,国际需求大大刺激了几种主要经济作物的种植——像茶、丝、棉、糖、花生和大豆。对冀-鲁西北区而言,棉花和花生处于非凡重要的地位。同时,因国际需求而扩大的生产,有的后来又被国际竞争所侵蚀……商品化了的中国农业,不再只受国内市场动向的影响,同时也受世界性市场的下降影响”。一般认为,这对于传统农业而言,当然是历史性的进步。
但是,在人地关系不可能改善的制约下,农业的种植结构调整意味着比较利益低下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下降,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满足基本生存的自给自足能力随之下降,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也随粮食的自给能力下降而难以保障。
1、种植结构的变化
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表现为农民从种植用于自给的粮食作物逐渐向种植经济作物转变。比如,河北、山东的植棉面积明显增长(见表1)摘要:
需求弹性较大而且受市场需求制约的经济作物面积扩大,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稳态结构。黄宗智[4]指出,“冀-鲁西北地区植棉比例,多至占总耕地面积的30%以上,还有许多占10%至30%……这样的种植规模,足以改变当地村庄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结构”。而河北花生的播种面积,1914-1918年达200万亩以上,到30年代,已超过400万亩。山东则由1920年的200万亩增加到30年代的500万亩。山东章丘和济阳县,花生种植达耕地面积的50%和40%,1924年有约90%的收成输出,大部分经青岛远销至马赛等地[5]。
2、粮食新问题摘要:面积下降和输入增加
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作物、园艺作物面积扩大,粮食作物面积在逐渐缩小。
25年间的种植结构变化是摘要:经济作物的比例上升明显,而粮食作物除玉米产量大而不断上升外,基本处于下降趋向。本世纪初叶粮食输入的提高幅度大于经济作物输出。输入粮食中,以经过加工的大米的增长幅度为最高,小麦次之,表明随经济作物增加,主要粮食需求只能靠增加输入来解决。农业的稳定性在商品化进程中退居次要地位。
3、农业的专业化区域种植
资料显示,20~30年代全国逐渐形成了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农业种植区域。如苏、鄂、鲁、冀、豫、陕、浙为主要棉产区;皖、赣、闽、浙、湘、川、滇为主要茶产区; 浙、粤、苏、川、鄂、湘、鲁、冀为主要蚕桑区,其中以浙粤为最大;鲁、豫、 皖、滇为烟草产区,主要种植美国烟草;东北为大豆产区;鲁、冀、粤、鄂、苏、桂为花生产区;长江流域为米产区;东北、鲁、冀、川、豫是小麦集中区。由此可以认为,我国传统农业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结构,因为专业化的生产和商业化的交换日益普遍而在不断改变之中。 占有土地较多的农民在种植结构调整中,逐渐向追求货币收入的行为取向转变。
二、农业商品率和农村经济的商品化
19世纪以来种植结构的调整,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率不断提高,而且区域差别和年际波动显着。民国时期我国农村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这一商品化程度可以从农产品自给、销售和购买各占的比例,以及生活资料自给和购买的比例等指标中看出。
1、农业商品率的提高及区域差别
卜凯[6]的调查表明,1921~1925年中国17处调查地的农产品总产量中自用和销售的比例达47.4∶53.6;其中北部为56.5∶43.5,而中东部非凡是东部的苏浙一带,农产物中自给和销售之比为37.2∶62.8,浙江镇海出售农产物的比例竟高达83.8%。另外值得注重的是年际波动,其中如河北盐山1922~1923年变动达25%。这些数据可能偏高,但仍然能够说明当时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传统特征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满铁的调查也说明,东北地区商品化程度相当高,而且耕作面积越大,商品化率越高。
另有资料显示[7],30年代全部农产品的商品率有所提高,惟独粮食例外。1931~1937年间,全国的商品粮在粮食总产量中仅占18%。按照商品率高低排序如下摘要:小麦29%,高粱25%,土豆24%,玉米19%,大麦18%,大米15%,小米10%;其他为18%。值得注重的是,农业发达而且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南方,大米的商品粮比例也相当低。这和南方在人地关系更为紧张的条件下经济作物占地较多有关。
2、农民的生活自给比例仍然较高
由于受剪刀差影响,农民生活资料中来自市场购买的比例,大大低于农产品销售的商品率。卜凯[8]20年代的调查表明,相对于农产品商品率的不断提高,农民在生活资料上基本上仍然处在半自给的状况中,自给部分占65.9%,购买部分占34.1%;其中北部自给部分为3.3%,中东部 58.1%, 北方农村的自然经济特色远较南方浓厚。但是进入30年代以后上述情况有很大改变。农民生活资料商品率10年间有了明显提高,而且南方更高于全国水平[9]摘要:全国农民消费的生活资料中购买来的粮食达35%,洋布29.9%,洋袜43%,煤油54.2%,肥皂34.1%,肥料26%,酒48.8%,香烟19.3%。 而江浙农民从市场购买的各类生活用品的比率明显高于全国水平,如浙江则为粮食53%,洋布51.9%,洋袜79.6%,煤油80.3%,肥皂81.5%,肥料52.4%,酒48.8%, 香烟35.1%,可见南方沿海地区农村对市场的依靠程度更甚。
此外,东三省农民饮食品购买部分呈现出和耕地面积增加负相关的态势,说明越是自给能力差的贫家(小于15垧)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中购买部分越多[10],所受的剥削越重。 这和上文提到其农产品商品率和耕地面积增加呈正相关恰恰相反。
冯紫岗的《兰溪农村调查》对购买的生活资料在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分布情况有清楚的反映。以上数据说明,无论总计还是分类,从市场中购入生活资料的比重大体从地主到佃农依次递减, 但佃农兼雇农购入的生活资料的比重明显偏高。其中,地主从市场购入总计达72.35%,佃农兼雇农达97%,雇农也达50.88%。贫富两极的情况截然不同,地主能够收取货币地租而且有支付能力;而佃农兼雇农则是由于从土地上获取的剩余太少,燃料、饮食无法满足最低需求。
3、农户收支的货币化程度
据卜凯[11]对全国七省17处各类农户农场支出情况的调查表明,二三十年代, 农户收支的货币化程度并不比现在低。平均起来,现金支出在自耕农达43.9%,半自耕农为42.7%,佃农达39.4%。另一方面在农民收入中,现金收入比例平均已超过非现金收入,而且,半自耕农收入的货币化程度高于自耕农,而佃农又高于半自耕农。
瓦格勒本世纪初的山东调查反映了使用土地面积和现金收入的关系摘要:1913年山东胶州各类农户现金收入对总收入的百分比排序摘要:42亩地的自耕农为38%,20亩地的佃农为28.6%,14亩的自耕农为24.5%。这也说明使用土地越多,收入的货币化程度越高。
种植结构调整、商品率提高和自给能力下降、收入货币化,农业和农村经济这3个方面在20~30年代的重大变化,为工商业和金融资本进入农村经济,以远高于地租的剥削率榨取小农剩余提供了条件。
三、商业资本对农业的剥夺
商业资本作为从农业提取剩余的主渠道,对农民的剥削程度远甚于地主的地租率,而且随上文所述之农村经济商品化提高而愈演愈烈。
1、商业资本的剥削方式
严中平[12]概括了五种剥削方式摘要:
第一种是从农民手里购买农副产品时,利用各种欺诈手段,取得价格上、数量上及至币值上的便宜。例如在山东、河北的烟产区,烟商用低估、压秤、索取佣金、支付贬值辅币、转嫁捐税负担等等方式,使烟农所得实际价格仅为名义价格的70%,在安徽商城和凤阳,只有50%左右。
第二种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相结合,利用农民的弱点,用奴役的条件贷给现金、原料、日用品或生产工具,使农民以被人为压低了的价格的农副产品抵偿债务。如江苏南通,外商将未成熟的棉花用“期买”的形式先行购买,其所估计的价格不及市价的30%~40%,若按利率计算,压价在50%以上。又如在广东茂名、东昌、阳山,有一种“放谷花”,谷价由当地商人估定,通常合市价的1/3 。在茂名借1元 ,4个月 还谷4 斗,价值超过2元;东昌、阳山多3月贷款,6月收谷,3元债收谷一担,约合5元。四川内江有“押青山”,以来年甘蔗预押和糖农(糖房), 分期取款,普通较时价低20%~25%,若毫无收成,至少按平年3~4分付息,顺延至下年交蔗。
第三种是用商品偿付农民出售的农产品,一般是品质极劣的商品,“这种形式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所有一般未发达的阶段所特有的”。如四川沪县、富顺,有的蔗农以蔗和糖房换糖,每100斤仅换糖3斤。江苏东台,当棉花收摘无人收买时,棉农为生活所逼,不时拿棉花换粮食和副产品,折价籽花每担5元,而以前的籽花是每担20元左右。
第四种是用生产者必需的原材料偿付农民出售的产品,以使农民同原料市场断绝联系,直接受制于商人。 如江苏南通,布商以棉纱向织户换取土布,每包18支纱作价比现金购买时高出0.3~0.5元,而每匹大布作价又比现卖时压低0.1~0.2元。
第五种是直接向农民分配原料,使商品生产者成了在家中为资本家工作的雇佣工人。河北高阳,织户无钱及原料,托人介绍到布线庄领取纱来织布,织8.5斤白布单人工一项就要9角7分,而钱庄所给工资最多只有9角,平均为8角。
2、价格剪刀差
衡量商业资本剥削程度的主要指标是价格差,一般用农民所得价格来反映。下表资料反映的是农民在终点市场所得的价格占销地价格的百分比(见表7)。
从上表可以看出,尽管有经营费用,商人的剥削的程度仍然可观。其中最低的仅为销地价格的不到一半。严中平还认为,表中农民得到的价格无疑是高估了的,因为这些价格中间包括着农民运往市场的运输费,也包括一些中间商贩的利润。而且由于商人的各种榨取手段,农民所得到的名义价格和实际价格还有一定的差距。陈翰笙的调查更表明,这种差距有时达1倍以上。
我们还可以通过各地乡镇农产品价格季节的指数变动来看商业资本活动的结果。商业资本在青黄不接时抬高价格,而在收获后压低价格,从这一高一低中商业资本谋取了超额利润。由于农业生产和收获的季节性特征,商业资本的活动可以使农产品价格成倍上涨,江西泰和的小麦价格指数差166.3%,湖北黄陂的小麦是144.9%,湖北远安的黄豆价格差是120%。可见即使在农村基层的乡镇,市场交易也相当活跃,商业资本可以得到颇丰厚利润。而分散的农民只能付出高价购买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出卖产品经常赶在低价时,所受的剥削也相当多。
个别地区的调查则更具体地反映出价格剪刀差的差距变化趋向。如江西南城县农民所得物价和所付物价的变动,可以反映出20~30年代随着工业化加速发展而出现的剪刀差扩大。
这些指数表明价格剪刀差在1937~1944年这8年间呈喇叭口状的扩大趋向是明显的。当然,抗战期间通货膨胀的影响不能排除,但是应该看到,农产品作为生活必需品,其在战时的价格上涨本来是应该大于其他物品的。
由于在农业的商业化进程中工商业资本对小农经济的过量剥夺,农村自然经济日趋解体,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越来越多地受制于市场,也必然无力承受市场供求变动和价格大起大落的摔打,许多人生活日趋艰困。如浙江蚕农无钱买桑叶,只得以糠果腹;甚至抱蚕入河。广东顺德50万蚕农(占全县人口50%),因丝价不及2/10,工料亦不足抵债而停工,20万女工入广州佃工或卖淫[13]。
四、农村借贷关系和金融资本活动
上文有关商业资本对农民的5种剥削方式中,已经涉及高利贷和商人结合的剥削程度远甚于地租率的情况。本段专门讨论金融资本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影响。
1、农村借贷普遍化
民国时期农村借贷关系已经频繁发生,据《农情报告》第二年第4期第30页的材料, 各地农村中农户借款的家数达56%,借粮的家数也达48%。全国各省的情况如下摘要:
上表可见,最多的察哈尔省借款的家数达79%,借款最少的河南省也达41%;借粮农户最多的广西达58%;最少的绥远、河北为33%。有的省借粮农户相对少是因为土地资源相对宽舒、土地产出率较高或种植结构并未商品化,所以粮食的自给程度较高。
2、各类农户负债的差别
各地各类农户负债不同。 金陵大学农经系1934~1935年对各地农村共14地区852户的调查表明平均负债发生率达71%,最高的安徽平均有80%农户负债,最低的江西也有57%。
从不同农户类别负债发生率比较来看,佃农高于半佃农,半佃农又高于自耕农,同农户的贫困程度一致,越贫苦的农民发生借债的户数越多。严中平汇集的同期资料也能反映这一趋向。
贫农的借债发生率在广西苍梧竟高达89.4%,最低的河北定县也达63%。但负债和商品化程度的关系则比较复杂。
广西苍梧1934年借款和借谷户在中农、富农和贫农之间的分布和上述情况不一致,借谷的农户也是贫农多于中农,中农多于富农。但是,借钱户高低排序则完全相反,富农达66.7%,不但多于中农,且成倍地高于贫农。这一方面说明拥有财产多少在借贷发生时所起的功能,可抵押财产越多信用程度高,越轻易得到贷款;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商品化程度越高的农户信用活动越频繁。
3、农户借贷用途
然而据金陵大学农经系1934~1935年的调查,农户贷款90%以上主要用于生活,其中佃农借贷用于生活的比例高达94%;用于生产的只有半佃农较多一些,也仅为11.4%。
上文的剪刀差和这个资料结合分析,表明农业面临双重困境摘要:一方面农业产出低价卖出,农民除了劳动力之外对农业的其他要素投入较少;另一方面农民要高价购进生活用品,贷入资金也只能大多数用在生活急需上。这似乎形成了一个促使小农经济衰败的恶性循环。说明农业的商品化对农民而言并不一定是历史的进步。
4、借贷利率
1933~1934年一般性借贷的利率的统计显示出借粮食年利高于现金借贷利率好多,多借用粮食的贫苦农民所受的剥削也更多。更严重的是借贷利率还在不断增长之中。
本世纪初至30年代的25年间利率在农村一直处于不断增长中。南方利率增长的幅度大于东北地区,按年度计算广东台山为最高,年增约24%。
表中数字表明,虽然存在年际波动,现金和粮食借贷的利率趋向都不断增长。其中,私人利率最高,年利达132%;其次是抵押贷款。而合作社的利率尽管最低,1938年仅为1.2,1946年也增长为4.1,年利仍然近50%;而且其贷款总规模所占比重太小(参见下表),对农民只是杯水车薪。此外,粮食借贷如折成月利计算的话,显然高于现金借贷。最高的1945、46年,6个月借钱还粮利率已达192%。不得不借粮度日的贫苦农民雪上加霜。
5、高利贷
据中心农业实验所对15省的调查[15],放贷者主要是地主、富农和商人,其次是合作社、银行和商店等各式的金融机构;传统的钱庄、典当和官方的合作金库等占很小比例。应该重视的是,银行、商店这些新兴的商业金融机构放出的高利贷比重在不断增加,而地主、富农及商人以及兴起不久的合作社发放高利贷的则在减少。其中银行占高利贷比重在8年间增长3倍。
6、高利贷的利率
这方面还没有完整的经过统计整理的材料,只能找到一些零星的记录[16]。实物借贷中,湖南衡阳的“标谷利”四五月间借谷1石,按当时最高价格折谷偿还,3个月便增加了3倍以上;江苏川沙的“翻扛子”和太仓的“利加利”, 除加几成计算之外,则是春季麦贱时折成麦,秋季米贱时又折成米,秋季偿还时也能增至3倍以上,第二年偿还甚至增加到10倍以上。山东鱼台的“青麦利”,青麦未黄时借粮,两三个月要借一还四。
借货币高利贷的利率也相当高,广州琼崖的“五钱市”借100元月利75元;四川宜宾的“金斗翻”是借洋1元,天天付息1角直到还清;湖南桃源的“孤老钱”,每月一对本,借1元,满月收2元,两月后还4元,以此类推;各地的“驴打滚”,也是到期后利息变成本金,又再生利,利上加利;河南新郑以1月为期,利率4-5分,期满未还,利率则按月递增;甘肃皋兰的“穿碾子”,期限最多一天,利息便20分,过期滚利;常熟的“放过洋(押头鸟)”以10天为期,也是利上加利。另外,还有的高利贷在借款时即扣下当月利息,或以少计多,河北临城就有“六顶十”的。
除了单纯的高利贷外,高利贷还和商业资本结合了起来,层层加深剥削。广东茂名有“卖地皮”“卖青苗”、“放谷花”,系收获前三四个月预卖田中的谷,谷价由田主估定,通常只合市价的1/3,合收获时谷价的1/2;山东鱼台的“赊牲畜”一般用现款20元可以买到的牛驴,假如赊买便须120元。
有的高利贷直接和地权和财产的抵押相结合,成为地主掠夺农民财产的手段之一。一般借高利贷用土地财产抵押,如期不能偿还,则财产为债权人所有。如湖北的“顶麦根”是以自己耕种的麦田作抵押,债主收田中的麦子为息, 本金则另外还;如无力偿还,债主就可将地出租,一直到债务还清才能赎回。江苏的“三道连”、绥远的“死契粘单”、浙江临安的“死契活票”,借钱时除要求写借契外,还要交出活卖契、地契或直接写下绝卖死契、田地绝卖契等,到期不能偿还,田地则归债主所有。山西中部的指产借贷,用价值114元的田地房产抵借15元,月利4分,限5月,如期不还,田地房产归债主等。
高利贷中也包含超经济强制,东北西安、西丰等县有佣还;广西有劳役利息,人身抵押和人口典当。劳役利息是借洋1元,为债主服务1天为利息,借满30天就要全年替债主服役;人身抵押是借钱时写明,到期不能偿还,须把儿女或本身押交债主家服役,通常月利6~7分,期限最多为1年,届期沦为奴隶者有的只能抵利息,还要另外交付本金去赎;人口典当则是借钱时把子女典当于债主,到债主家做工以抵偿利息,如期满后无力偿还债款,则继续为债主服役,债主可为其嫁娶,生下子女仍为奴隶。广东罗定,有“押妻女”,借钱时妻女抵押给债主,如在债主家怀孕,所生子女归债主所有,偿还时只能赎回原来的妻子;如无力赎取,妻女便归债主所有。
五、启示
1 随着本世纪30年代社会政治的初步稳定,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共同功能下明显加快,从而拉动农业种植结构有了明显调整,农业的商品化市场化、农户收支的货币化程度也有所提高,专业化区域种植使农业剩余有可能形成一定规模,农村市场开始活跃,商业和金融资本也有了发展机会。
2 商业和金融是农业剩余流出的主要渠道。这二者都易于和占有农业剩余较多的地主相结合;但和地主之不同在于,它们处于和农业完全对立的地位。因此,其合乎经济理性的行为是在小农经济剩余少而且分散的条件下,采取扩大剪刀差和普遍高利贷的方式过量剥夺农民。
3 高利贷所代表的金融资本,加上不断直接鲸吞着农业剩余的商业资本在农村经济中的功能,和30年代中国工商业资本原始积累加速的情况相辅相成,同时期农村拥有生产资料的比例和富裕程度正好和商品化进度和负债率逆向而动。尤其值得思索的是摘要:大多数农民借贷都主要是为了应付生活急需,而不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各类农户在种植结构调整和农业的商品化程度提高之中并没有受益,工商业资本原始积累是以牺牲农业和小农破产、社会矛盾激化为代价的。
由此可以认为,旧中国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稳定格局冲击最大的,是在国家追求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从农业提取剩余最多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金融资本。所以,中国的农民革命,主要起因于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
注释摘要:
[1]本文由农业部农研中心温铁军提出探究假设、组织调研讨论并统稿, 中国农业大学冯开文收集资料并起草初稿,96级部分探究生参加农村调查。龚启圣、俞家宝、詹玉容、张晓山、周其仁、蒋中一、朱守银、张照新等对探究思路的形成给予指导或参加观点讨论。本文和已经发表的“近代中国农村土地的两权分离”(见《??》1998年第4期)为上下篇。
[2]亦称“人口陷阱”。纳尔逊50年代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会被人口的过快增长抵消。
[3]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第124页。
[4]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第132页。
[5]章有义,《近代农业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232页,227页。
[6]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第275页。
[7]德•希•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第205页表。
[8]卜凯,《中国农家经济》,页525。
[9]《农情报告》4卷8期,第198-206页(1936年8月),具体反映了30年代农家购买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的情况。
[10]伪东三省铁路经济调查局《北满农业》274页。
[11]同上。
[12]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30-334页。
[13]见陈翰笙等,《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1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451-452页所引许涤新,《动荡崩溃的中国农村》,1932年12月8日。
[14]表16是由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页1108-1009、1030-1031以及续编页824的材料,陈翰笙,《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吕平登,《四川省农村经济》页452等的统计材料汇编而成。其利率增长百分率由期初利率除期末利率乘以100再减去100而得。
[15]表17、18是国民党中心农业实验所对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河南、陕西、 甘肃、青海、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宁夏15省的调查结果,见于《统计年鉴》1947年,页93-94,更细致地反映出了借贷期限,借贷来源以及借贷利率的变化。
[16]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48-3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