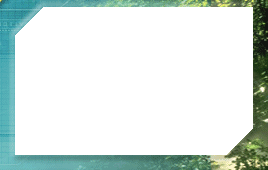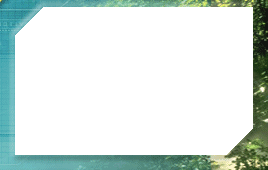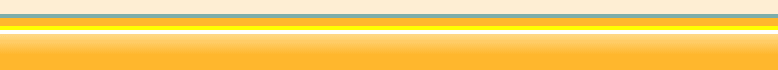到底什么样的组织才能让农民自己决定?种种现实问题让我们对农村治理组织产生了大大的问号?
在加速市场化进程的南粤大地上,富有强烈个体意识的广东农民,对个人权益保障探索的脚步从来没有因政策环境改变而停止,例如蕉岭县“四权”农村治理创新实践——村务监事会制度、干部家访制度、干群对话制度、村代会召集组制度。
可能有人会认为这种民主有残缺,担心由纪委推动的村民自治模式能否持续。中国的民主要外烁内生,唯有在民众意识中植下民主基因。但任何一次民主的实践,都是对民主思想的体验。参与式民主也是代议政治的一种补充,由大学、媒体、政府、民间共同主导的蕉岭试验,并非纯粹从上至下的,它显示了中国老百姓的民主潜能,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民主政治的微光。
广育村村委主任黄坤荣说:“要管理好村庄,不搞民主是不行的。”监事会制度的建立、南农实验民主示范区的建立,使村民体会到了民主的必要性。
“要民主”还是“被民主”?
是“让农民组织起来”,还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这是现实中体现农民民主被动关系最明显的两句话,体现了农民是“要民主”还是“被民主”。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陆雷认为,在行政机构强力掠夺农村资源的建国后初期,严密的党政组织延伸到乡级,通过“苛捐杂税”给养上级财政。到现在政治手段弱化的时代,农业税被取消之后,需反哺农村之时,如新农保等制度建立,从中可以看出这样的现实,让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前提是公民社会的培养,即公民必须有结社权,有了共同维权的组织,方可谈民主,要不然只能“被民主”。
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所长何增科认为,“被民主”指的就是政府自上而下、自外而内推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有关制度安排。“我认为,与组织农民合作不同,农民合作组织是一种基于农民内在需要而建立的组织,是农村社会的自主性整合。在这种合作和组织中,自始至终都体现着农民是合作的主体。”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徐勇会上说。
南农实验课题组的研究人员调查发现有30%左右的村民不知道村里存在监事会, 40%的村民则认为协助村干部工作是监事会的最主要职能,而监事会参与村务监督主要靠村委会的邀请,事实上如果村干部想要绕过监事会自己处理村务仍然很有可能。
由国家组织乡村社会和村民的力量进行民主监督,并不能解决“村民的力量不够大、村民的监督能力不强、怕得罪村干部”的恶性循环。
“要民主”成为农村自治组织建立的引擎!
“要组织”还是“被组织”?
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在真正的宪政体制中,只要实行地方自治或者社区自治,基层政府就是自治组织,没有两者只能居其一之说。但这种自治组织是一种特殊组织,即公权力组织,从理论上讲它要代表所在地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可能只代表其中某个群体的特殊利益。他认为“自治比民主更重要”,要解决治理难的根本办法仍是解决农民权利缺失问题。
权利缺失,使得农民可能“被组织”。
徐勇教授在会上谈起安徽岳村实行农民合作组织实验时,分析认为中国农村是以家庭为组织单位的相对封闭式结构,中国农民善于在家庭内合作,而家庭外合作能力缺乏。历史上的合作是农民被组织、被合作,依靠的是外生力量,而不是农民的主动合作。
民主是随着利益走的。利益就像大旗,民众的监督权要跟着大旗一路狂奔。
正如徐勇教授此次在会上所讲:民主化治理是大趋势。农民只有通过组织来实现自治!农民参与必须靠组织!
蕉岭县芳心村村民之所以愿意参加干群对话会,是因为会上所讨论的内容,与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例如,干群对话会曾经讨论过芳心村集体林地承包给外村人的事宜、集体土地拍卖事宜。
“要组织”的意识增强,克服了个体化参与民主的无力感!
能否做到“三权制衡”?
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所长何增科在会上说,要实现组织创新,需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分离彼此制约的要求, 对议事决策机构、执行实施、监督监管机构分设进行大胆探索。而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制衡,这是实现农村治理方式和治理过程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方向。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高新军在会上指出,由于大量的农民面对的是5-7人的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干部,这些干部领着“工资”,干着上传下达的事情,他们虽说是农民选举产生的,但是他们更像是农村中的官僚, 对于为农民服务,他们既力不从心,又缺乏动力。这样,在行政村与农民之间,就出现了自然村层面上的组织断层。弥补这个断层,现有的组织资源中并没有现成的答案,这就需要进行组织创新。
农民的利益诉求是通过组织来表达,打破决策、执行、监督的“一揽子”政治,需要组织间的制衡!从“村委会说了算”到“大部分人说了算”,实现权利主体的转移,需要乡村熟人社会探索出新道路。
在会上,著名杂文家鄢烈山先生提出, 浙江温岭民主恳谈模式是宣传部主导的, 青县模式是组织部根据组织特点进行的“村代会制度”的探索,而蕉岭模式是当地纪委推动的,这都是三个部门根据自身的职能推动的农村治理制度。现在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创新和推动。只要在法律框架之内干实事,落实比什么都重要,比争什么东西都重要。
看来,要真正实现组织创新任重而道远。而真正能实现“三权制衡”,仍需要制度革新!
农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组织?
上两个世纪的三十年代,托克维尔在美国考察的时候,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一群互不相干的美国人在路上遇上了一件事情,我们假设是山体滑坡了,这些人会马上组成一个山体滑坡处理委员会,分工负责、志愿协同来处理这件事情。托克维尔于是感叹:要是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正比地发展和完善。
农村组织建设到底由谁来组织?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似乎是毫无疑问的:当然是农民自己来组织了,谁也不能包办代替。可是面对现实中由政府力量推动的组织建设,我们又将如何破解?这也是组织创新中引申出的一个重大命题。
有些学者认为让乡镇一级实现自治,而县域实现民主,形成代议政治,乡镇直接出派出机构即可,对此,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国英认为,连派出机构都不用设置,就让乡村实现自治。
组织创新需要公民精神
在中国历史上极权与民粹政治交替演进中, 农民成为暴力革命的重要力量,学者一致认为就是没有形成公民意识。 为什么经过几千年演进,我们都跨不过这道鸿沟呢?这得归结为农民从来就缺少真正由农民自发力量建立的民主组织, 有的只是与皇权体制相应的宗族或类宗族生活。由于缺少民主生活训练,人们的合作意识、平等观念和民主习惯也就很难养成,而这些精神是公民社会的支撑。从这个意义来说,进行农村的组织建设,使每一个村民都有社团的生产或生活,无疑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