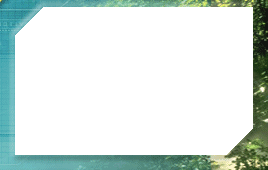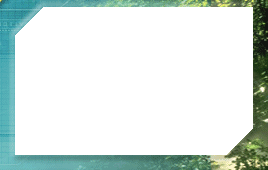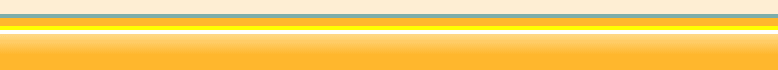相关链接:
吕新雨:列宁主义与中国(17-10-20)
十月革命:人类历史新纪元(17-11-22) 吕薇洲:十月革命的核心精神(17-11-22)
列宁如何建立一个新世界?(17-11-22) 十月革命的偶然性与必然性(17-11-22)
田曦:如何看待社会主义(17-11-22) 辛向阳:列宁的政权建设启示(17-11-22)
聂运麟:论立宪会议的解散(17-11-22) 童晋:西方国家纪念十月革命(17-11-22)
俄共对十月革命认识与评价(17-11-22) 21世纪俄罗斯马哲的境遇(17-11-22)
十月革命对拉美共运的影响(17-11-22) 布里:夺取政权后怎么办?(17-11-22)
张广翔 刘玮 翻译
1917年十月至今已近百年, 我们的国家高举十月革命胜利的旗帜存在70余年。很快, 俄罗斯及许多其他国家将迎来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百年纪念庆典。
但目前, 一些自由主义阵营的新闻媒体和政界开始混淆抹杀革命历史事实真相。用十月革命的偶然性来伤害自己的民族。人的主观行为具有客观逻辑性, 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全面深入地研究一连串事件中的内在必然联系。1917年十月革命的客观逻辑性由一系列历史事件演变而成, 它们与普通民众及著名政治家的愿望、行动密切相关。
革命源于何处?
今天的“历史学家”允许自己这样说:二月革命始于排队买面包引发的混乱场面。这里复述一下皇后А.费多罗夫娜对此事的评价。她在1917年2月25日给丈夫的信中写道:“城里罢工和无序状态比宣传严重得多。这是一次流氓行为, 年轻人为没有食品奔走叫喊, 仅仅是为了联合那些不满的, 以及妨碍他人工作的工人。如果天气足够冷的话, 或许, 他们所有人都只能待在家里, 那该多好。”[1](p.144)
皇后认为, 如果天气足够冷, 那么俄国将不会爆发革命。革命始于某些人的歇斯底里, 或者这些人需要表达自身对客观现实的不满情绪, 抑或是绝望, 抱怨声震耳欲聋, 最后导致暴乱。皇后似乎不知道, 队伍的不满和愤怒引发了严重的后果, 社会骚乱和动荡的产生有着深刻的背景和原因。皇后好像未曾想到, 让这些少男少女愤怒的不仅仅是缺少食品, 还有他们的父亲兄弟为着不明确的目标在战壕里浴血奋战, 浑身血肉模糊。
要知道战争是十月革命史上最重要的因素。没有世界大战就不会有十月革命, 那些史学的和其他学科专家忽略的恰恰是这个因素。他们坚信, 从布尔什维克发起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 生活已变得十分美好。А.Ф.克伦斯基认为, 如果没有“Л.Г.科尔尼洛夫叛乱”, 就不会有“十月革命的爆发”。可以满怀信心地说, 如果没有皇室奸党坚持让俄国参加世界大战, 那么, 不仅十月革命, 就连二月革命也都不会发生。俄国并没有像沙皇预想的那样, 已经做好迎战的一切准备。缺乏现代化武器装备, 道路交通无法担负军事运输任务, 每1—2名炮兵只能配给一发炮弹。
当俄国炮兵没有什么可用来回报德国人的时候, 士兵们却试图在违者处以死刑的恐惧中开始发动攻势。1917年年初, 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最终陷入战争疲惫、物价上涨、投机倒把、排队买面包之境地。此后, 成群结队的妇女开始打砸摊位和商店, 引发社会动荡。2月18日, 彼得格勒布基洛夫工厂工人宣布罢工, 该事件是导致整个事态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应对措施, 政府解雇了3万名工人, 导致他们失去了生活来源。2月23日 (3月8日) , 莫斯科爆发了由渴求食品的妇女, 以及前线归来的战士们组织的大规模游行示威。2月25日 (3月10日) , 经济性的消极怠工发展成以“打倒沙皇”“推翻专制”“远离战争”为口号的政治大罢工, 工人同警察及宪兵发生了冲突。2月25日的罢工已经超过30万人。难道这一切只是愤怒群众一种歇斯底里的爆发吗?最后军队决定驻扎在彼得格勒, 倒向人民一方。2月25日, 尼古拉二世从大本营向彼得格勒军区的指挥官发出命令:“明天必须制止首都群众性的骚乱。”但是, 荒漠旷野里大声疾呼根本徒劳无益:没有人愿意保护沙皇, 专制制度注定走向失败。
接下来整个时期的政治军事力量, 其中包括卫国战争以来, 保存和发展起来的政治军事力量土崩瓦解, 君主制度思想已不复存在。3月2日, 沙皇签署了退位的相关文件。1917年二月革命就这样发生了。这是一场民族革命, 没有人可以对不想按照旧方式生活的人民妄加指责, 短短几天, 革命队伍就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的统治。
双重政权是十月革命爆发的先决条件
根据俄罗斯政治思想学说, 俄罗斯本应该实行共和国制。但是, 颠覆了沙皇专制统治的共和国政权在二月革命后表现得非同寻常。当得知国家建立两个政权, 即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后, 革命群众聚集在举行杜马会议的塔夫利达宫, 他们以同等的热情欢迎两个并存政权。1917年3月1日, 两个机构的领导人达成协议, 组建以Г.Е.利沃夫公爵为首的临时政府, 但这并没有结束国家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临时政府不能消灭苏维埃的存在, 因为苏维埃掌握着军事实权, 要知道士兵委员会加入了苏维埃, 实际上, 军队隶属这个军事委员会。所以, 在必要时, 苏维埃能够立刻宣布自己是全民族统一政权。然而, 苏维埃的领袖们, 即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及社会革命党人认为, 俄国革命应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这是资本主义自由政府的一贯做法。
彼得格勒苏维埃领导人的理想信念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主观因素, 影响力度相当于革命情绪高涨的人民群众对其信赖的程度。掌控苏维埃领导权的那些“社会主义者”, 实质上对资产阶级政权做出了让步。这种形势最终无路可走, 首先因为临时政府无法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主要任务, 即土地与和平, 二者的相互关系十分密切。俄国的双重政权并存就这样为十月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前提条件。如果不解决土地与和平问题, 资产阶级革命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结束的, 也结束不了。沙皇专制统治被推翻了, 但主要问题却没能得到有效解决。这里应该寻求如下问题的答案:这是一场革命还是一次变革?究竟是谁能够又如何解决这些意义重大且迫切的问题呢?
列宁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这份提纲里写道:“革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 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 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 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2](p.114)
列宁看到的形势就是, 革命要经历第一第二发展阶段, 革命就是一种过程。只有从自身内部的必要性出发, 作为过程的革命才能够得到理解。第一阶段没有解决的任务促成了第二阶段的发生。
今天, 当在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的领导下, 无产阶级最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任务时, 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要解决的任务就是“揭露”上述过程的反常情景, 为此, 他们建议放弃这一理论思想自身的主客观前提条件。例如, 《20世纪的俄国史》认为:“从20年代到80年代 (包括80年代) , 祖国历史编纂学的所有流派都试图明确定义革命的‘前提条件’这一概念, 但这些尝试和努力可以被视为是徒劳的失败之举。无论是主客观‘前提条件’明显的相互依赖性, 还是革命规模、深度和结果之间的依附关系, 它们都未被发现和揭示出来。‘前提条件’理论思想强迫我们接受有关革命的客观规律性、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 (十月革命后) 、进步工人阶级起到的主导作用等结论。”[1](p.147)
事实上, 对十月革命的客观前提持拒绝态度导致承认革命爆发毫无缘由可言。并且从客观前提方面否认十月革命, 意味着需要求出主观因素绝对极大值, 即绝对主观的看法。因此, 由于我国“新”历史编纂学的发展, 我们再次从作为革命先决条件的土地与和平问题转向布尔什维克邪恶意志及渴望政权的道德性问题。取代历史事实这一历史学科的“粮食补给”, 我们在那些当代历史学家身上寻求到关于革命前历史时期“世界矛盾”这一抽象论断。如果从具体的事实中得出抽象概念, 那么无论什么情况,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得到“论证”。但历史事实终究值得深入挖掘和研究。那么又有谁能够按照逻辑演进次序将革命进行到底呢?在《20世纪的俄国史》中, 比起革命全部的“主观”和“客观”前提条件, 沙皇的个性反而得到更多的关注。但是, 革命敢于直面沙皇专制统治, 革命并未察觉其勇敢的挑战精神之存在。或许, 克伦斯基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
自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以来, 农民的土地问题自始至终悬而未决:农民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 获得的却是没有土地的自由, 土地依然留在地主手中, 这些地主老爷甚至还霸占了部分村社的土地。在俄国中部地区, 分给农民的平均份地大约1俄亩。正如农夫在伟大的民主战士Л.Н.托尔斯泰《教育的果实》中抱怨所说:“老爷, 发发慈悲吧, 我们的土地少得可怜, 连小鸡都无处放养。”
1905年革命以后, П.А.斯托雷平着手解决农民问题, 但是, 他无法实施改革, 因为他得不到来自上层和下层社会的全力支持。斯托雷平对待改革的态度“开始十分平静, 接下来则完全否定”。“平静”意味着上军事法庭、肉刑、上绞刑架。因此, 斯托雷平留在人民印象当中的只有“斯托雷平式的领带”和“斯托雷平式的车厢”。这就是今天临时政府面临的问题。
但是, 土地与和平两个问题息息相关。俄国深陷帝国主义战争的泥潭, 她无法将战争继续下去, 因为国家已消耗殆尽全部资源, 军队涣散, 作战能力低下。由于维持国际秩序的义务以及沙皇政府欠下的巨额债务, 俄国无法从战争中脱身。临时政府承担了全部债务并提出“战斗到最后胜利时刻”的口号。
当然可以战胜条顿人 (泛指日耳曼人及其后裔, 或是直接以此称呼德国人) , 但如何强迫士兵作战才是问题的关键。士兵就是那些期望临时政府出面解决土地问题的农民。而这个政府只会空许诺言, 答应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并推迟到立宪会议召开的时候。总之, 俄国社会矛盾重重, 盘根错节, 乱得一团糟, 只能用利剑才可以斩断死结。换言之, 革命应该步入第二阶段, 其中的必要性就在于:自由的临时政府并没有能力解开这些矛盾死结, 十月革命后, 种种矛盾只能随着革命进程的发展而日益加剧。
从危机走向危机
历史事件的前提条件本身是先前发生事件的后果。抽象理论脱离历史客观现实便没有了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 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 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 它们绝不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3](p.31)。
已谈到的战争因素对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具有决定意义。1904年日俄战争催生了1905年革命, 而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陆军海军部长克伦斯基同全体将领发动的1917年毫无准备的夏季进攻是革命的重要阶段。正在捷尔诺波尔的克伦斯基本人亲自发出进攻令。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全国处在狂热的期待中。我们的军队是否开赴前线?无论谁都不想冒险回答这个问题。”[4](p.202)
“对于军队开赴前线参战并在没有任何把握的情况下发出进攻命令”, 只有一个毫无责任心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克伦斯基写道:“说句实话, 准备进攻的第7和第11集团军的形势并不令人满意, 我们只能报以良好的期望。数个师团意欲谋反, 拒绝接受进攻令, 许多作战团只是表面和口头上服从命令。一些军官对进攻令几乎持藐视的态度, 另一些军官则公开破坏工事的修筑。”[4](p.203)
近些年, 许多学者纷纷著书立说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百周年, 其中谈道:“凯旋的俄国军队的胜利果实被‘窃取’了。”究竟谁是罪魁祸首?对此我们并不完全清楚:要么是沙皇及其佞臣奸党, 要么是“布尔什维克”。这就是1917年7月13日《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消息报》刊登的《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中读到的内容:“不负责任地巧言惑众, 夸大宣传已经在前方战场结出血淋淋恶果。仇视、敌对和混乱无序弥漫全军上下。而军队的兵力、战斗力就像幻影一样忽然消散了。军队被切断, 孤立无助, 伤亡惨重, 难以数计的战士向敌军投降……我军节节败退, 战事每况愈下, 军人在疯狂地逃离和躲避战争。我们为俄国和革命的命运前途感到担忧, 为战败感到耻辱。”[5](p.27)
军队上下士气不振, 完全丧失了爱国主义热忱。克伦斯基亲自承认:“官兵的内心深处已经不再燃烧着愤怒的火焰。我们十分清楚, 这些官兵没有习惯作战的感受, 每一次战役来临前, 他们多么艰难地承受这一切, 内心充满了惶恐和担忧的思绪。人们似乎感受到心灵深处难以愈合的伤口在流血。军官们到最后时刻都不确定, 是否派战士去冲锋陷阵?战士们站在自己角度同样不断地反问自己:是否值得去冒险送死?尤其当后方家园是先辈们几代人的梦想实现才换来的宁静生活的时候。”[4](p.204)
克伦斯基指的当然是土地问题, 临时政府只是口头承诺解决这一问题。并且这个历史见证人不是随便的某个“布尔什维克”, 而是对将战争进行到底、战斗到最后胜利时刻感兴趣的人。但无论是谁, 其中包括克伦斯基本人在内, 都深深怀疑胜利这一天能否到来。军队控制权从临时政府手中滑落。
早在4月, 第一次政府危机就已迫近。临时政府是最具民主性的政府:“今天的俄国是世界上所有参战国中最自由的国家。”[4](p.349)但是, 自由是普通生活最大的福祉, 与战争和军事组织水火不相容。著名的彼得格勒一号命令 (1917年3月1日) 第4点指出:“国家杜马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应该得到贯彻和执行只能是在以下情况:当它们与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颁发的决议和命令不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6](p.59)
这一决议意味着军队归顺苏维埃。喀琅施塔得拒绝接受临时政府任命的委员, 波罗的海舰队全体军舰和司令部代表选举产生了波罗的海舰队中央执行委员会。此举使波罗的海舰队摆脱了临时政府的束缚, 从此不再听命临时政府的指挥。可以说, 喀琅施塔得地区的政权已经归由苏维埃掌握。
这一切必然引起诸位将领的反应, 随后就出现了所说的科尔尼洛夫叛乱。临时政府处在科尔尼洛夫军事独裁和革命人民的夹缝间, 只能去遏制科尔尼洛夫军事独裁的野心和不良企图。革命人民越来越倒向布尔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已成为能够提供任何一方平衡的中坚力量。
二月革命的后果之一是军队生活民主化, 这使前线形势变得更加严峻。4月18日, 外交部长П.Н.米留可夫向外界宣称, 临时政府决心将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时刻。但群众的反战示威游行却成为对这一切的有力回击, 米留可夫和时任陆军海军部长А.И.古奇科夫被迫提交辞呈。
1917年5月5日, 临时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经过长期谈判, 双方协议组建新的联合政府。新联合政府成员由10名部长、自由资产阶级利益代表, 以及6名社会党的部长组成。社会革命党领袖В.М.切尔诺夫得到一个农业部长的位置, 克伦斯基捞到陆军海军部长职位。
新联合政府许诺开始举行谈判, 订立和平条约、制定农业改革方案、对经济采取国家监控措施。但是, 生产仍然持续下滑, 不同社会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早在1917年1月, 专家们就写道:“食品问题搞乱了, 比以前更加错综复杂, 越来越没有希望……土地分配已暴露出自己的不足, 而食品行业……已化作整个帝国的灾难。”[7](p.338)
在西南战线的加利奇亚进攻遭遇失败后, 俄军又迎来不断重复发生的危机。1917年7月2日, 立宪民主党的部长提出辞职, 其援引的理由是“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政府要求实行广泛的自治。立宪民主党人想向政府争取到更加严厉的政策和措施以镇压革命群众:解除工人武装、将首都卫戍部队参与革命的军队开赴前线、禁止左翼组织活动等等。将部分革命队伍从首都调往前线的企图引起了一些工厂的革命工人和士兵的示威抗议。喀琅施塔得水兵发动起义, 加入工人士兵的反抗队伍中。
1917年7月4日, 彼得格勒聚集了近50万人, 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7月3日夜, 一些军队的军事委员会发出武装推翻临时政府, 将企业、银行、仓库、商店等全部征用的号召。部分市区发生射击事件, 有人员伤亡, 但这只是一次自发的起义, 并没有推出关于武装起义的总决策。起义遭到从前线撤回的军队的镇压。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支持临时政府的行动, 结果, 委员会站在了反革命一方。孟什维克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全面展开街垒战。人们怪罪赞同停战的布尔什维克收受了德军总参谋部的贿赂, 发布命令拘捕列宁, 布尔什维克转而陷入非法的境地。
7 月8日, 克伦斯基还在主持临时政府工作, 12日, 他却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 赴前线去执行死刑, 18日, 他罢免了“自由主义的”А.А.布鲁西洛夫总司令的职位, 任命科尔尼洛夫担任总司令。克伦斯基的目的在于实行独裁。但究竟是谁能够成为这个独裁者呢?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二人都在觊觎这个位置。
布尔什维克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但是党的队伍急速壮大。如果说二月革命开始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 的人数数量不超过2.4万人, 那么, 到5月已增至10万人, 同年9月, 人数已达到35万人!据统计, 仅在一艘名为“共和”号的战列舰上就有600名布尔什维克。这意味着, 强大的海军战舰已经在布尔什维克的掌控中。所有这一切都是和平宣传, 不是暴力行为的结果, 暴力行为只适用于为数不多的人, 他们不仅不屈服喀琅施塔得号巡洋舰全体起义士兵的意志, 还千方百计地欺辱起义的官兵和海军上将威廉。
8月12—25日, 临时政府在莫斯科召开了国务会议。会议号召团结一切力量胜利结束战争。参加会议的有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的同盟者, 也有竞争对手, 但双方力量相差悬殊。一群军队的指挥员、哥萨克、外资支持的大工业家、上层官僚、知识分子、自由大贵族和地主纷纷要求实行强权统治、严明纪律、维护官僚和贵族的利益。这些人认为革命已经结束, 现在的话题只涉及巩固大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满足他们的利益要求。
工人运动中隐蔽的机会主义“革命民主派” (中派) 倡导的革命纲领含混不清, 克伦斯基将自己归入这一派中。社会主义党的代表没有用例行的革命纲领去加强“赢取革命胜利”这个常挂嘴边的借口的感染力。无论怎样, 布尔什维克都没有派代表在会上发言。应该特别强调这一历史真相。到
1917年秋, 在没有布尔什维克参与的情况下, 俄国政治界独裁的思想, 换句话说, 就是波拿巴主义思想已发展成熟。
临时政府制定政策时实行了更加严格的计划, 这样做与前方战事恶化有很大关系。在检查了西南战线军队的装备、军需供给、士兵状况后, 军事委员М.菲罗年科和Б.萨文科夫 (臭名昭著的反革命恐怖分子) 7月11日电告克伦斯基, 电文如下:“我们感到自己良心上有责任有义务声明,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没有选择和退路:对于那些拒绝冒死捍卫祖国、土地和自由的人就应该判处死刑。”[5](p.27)军事委员的到来本是为了鼓舞士气, 但却决定实行集体枪决。克伦斯基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在这千钧一发时刻, 我完全赞同西南战线军事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的正确决定, 这是真正革命的和最正确的行动。”[5](p.27)
克伦斯基没有别的出路可走。他那句“伟大的爱国主义浪潮”至理名言已经变成公开叫嚣的谎言。这里还需要举出第11集团军总司令巴鲁耶夫发来的一封电报:“了解到军队的士气和精神状态, 我十分惶恐。使我大为震惊的是, 我们的祖国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和耻辱?全体高级将领和军官什么都做不了, 如何去牺牲和奉献自己的生命。政府宣告第14条 (也就是就地枪决的权利) 不能执行, 因为单凭个人单枪匹马, 指挥官们难与成百上千有意逃亡的武装人员抗衡。作为祖国忠诚的儿女, 我应将自己的生命献给祖国, 自己有责任向政府报告实情, 俄国民主和革命正处在危机中。”[5](pp.27-28)
看来, 新民主政权已经做好准备向士兵开枪射击。但是, 判处死刑的命令已经失效, 因为要射击枪决的是成百上千拒绝英勇作战的武装人员。官兵之间的矛盾早已激化, 早在1917年2月, 由于军队实行民主化, 已经不是军官向士兵射击, 而是又开始惩治军官, 首先是那些折磨和侮辱士兵的军官。
十月革命后, 当Г.В.普列汉诺夫领导的孟什维克开始叫嚷什么“恐怖的布尔什维克”的时候, 列宁反击说:“先生们, 你们的克伦斯基在前线恢复了死刑, 这不是恐怖吗?先生们, 你们的联合内阁因作战中士气不振而用科尔尼洛夫之流的手, 枪杀了整团整团的士兵, 这不是内战吗?先生们, 你们的克伦斯基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以进行‘有害的鼓动’为罪名, 仅在明斯克的一所监狱里就监禁了3 000名士兵, 这不是恐怖吗?先生们, 你们扼杀了工人的报纸, 这不是恐怖吗?区别仅仅在于:克伦斯基、阿夫克森齐耶夫、李伯尔唐恩之流同科尔尼洛夫、萨文柯夫之流勾结起来对工人、士兵和农民实行恐怖, 是为了一小撮地主和银行家的利益;而苏维埃政权对地主、奸商及其奴仆采取坚决的手段, 是为了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利益。”[8](p.189)
在更加严格要求前线纪律的情况下, 克伦斯基尽管前去与将军们会面, 但他只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同这些人清算旧账。“战争最初三年的一切不幸、灾祸、耻辱, 对于这些人来说再也不存在了。他们更倾向于将所有这一切, 其中包括彼得格勒7月事件的起因, 看成是革命中唯一绝对的因素及革命对俄国士兵的影响。佐利塔乌、华沙、科夫诺、佩列梅什利、萨恩、科韦利、米塔瓦等等, 等等, 所有这些城市似乎重来都没有过……对一切新生事物心怀憎恨心理而酿成的苦酒让这些明哲老人感到头晕。军事首长从来没有向俄国及临时政府提供任何的建议与帮助。从另一方面看, 邓尼金将军第一次勾勒出‘复仇’计划, 这支反动军事力量为‘美好未来’谱写乐曲, 以此鼓舞众多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赞同者”[5](p.32)。这从1917年十月加契纳侦察委员会审讯记录的补充内容中可以看出, 10年后的克伦斯基都做了些什么。一切表明, 在当时的情况下, 当着侦察委员会的面, 他并不能说出什么。克伦斯基写道:“我在想, 莫斯科会议表明, 关于民众为追求更加正确的方针而有可能脱离临时政府的假说是一种危险的空想主义, 因为这样的梦想是不能得出结果的 (是不能得到实现的) , 它们只能更加激发民众愤怒的情绪, 并且对其他社会阶层更加不信任。”[5](pp.57-58)
总体上看, 克伦斯基对“群众”的态度同保守反动派一样, 应该将这个“野兽”关在笼子里。但是, “群众”并不愿意被困在笼子里。因此, 克伦斯基认为, 1917年10月的“群众”起义具有“反革命的”性质。
8月12—15日莫斯科会议上, 军方和临时政府未能达成统一意见。克伦斯基写道:“过去的不到一个月, 军队首领亲自用不服从上级最高政府指挥的行动做出了表率。因此, 每一个携带武器的将领拥有的权力得到确认, 按照个人理解去行事做事。”[5](p.89)
“科尔尼洛夫叛乱”及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临时政府威信下降, 布尔什维克的威信就会上升, 而科尔尼洛夫将军正是造成这一切的推手。之后, 列宁说道:“科尔尼洛夫叛乱和接着发生的事变都是切切实实的教训, 促使十月革命取得胜利。”[9](p.2)就连克伦斯基也没有虚度光阴, 在美国写下了整本的《科尔尼洛夫叛乱》。
今天, 自由派“政治学家”对这一切的评论是, 德国提供资金资助布尔什维克武力夺取了政权。但列宁的观点也是可以接受的, 科尔尼洛夫叛乱促使布尔什维克采取了夺权的行动。
8月26日, 科尔尼洛夫将А.М.克雷莫夫的哥萨克骑兵第三军团从前线调回派往彼得格勒, 大名鼎鼎的“野蛮师”并入这个骑兵军团, “野蛮师”的士兵都是从高加索山地民族中选拔招募而来。该支部队的目的是镇压和平定群众的革命情绪, 驱赶委员会, 建立军事独裁政权。作为回应, 彼得格勒组编了红色近卫军部队以保卫首都, 人数达6万。布尔什维克在事件进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当布尔什维克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之后, 克伦斯基以沉默“原谅”了布尔什维克, 因为他们在过去是唯一一支抗击反革命叛乱的革命力量组织。驶向彼得格勒的军列因为没有战事而停了下来, 军队接受了宣传教育, 他们拒绝前往彼得格勒镇压革命。克雷莫夫开枪自杀, 哥萨克返回家乡———“静静的顿河”。但是在整个事件中, 克伦斯基和临时政府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这个问题至今依然令人费解。扑灭叛乱后, 克伦斯基命令逮捕科尔尼洛夫及其他将领, 他们被送到贝霍夫市, 但被捕人员的状况不是十分清楚。给人的印象是, 他们没有遭到惩处, 而是被保护起来以避开愤怒的人民群众。在这种情形下, 克伦斯基自身的处境变得相当“复杂”, 他写回忆录明显是为了证明自己, 自我辩解。他意识到终将失去权力, 因为既不能依靠越来越倒向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人民, 又不能依靠全体将领的支持。要知道, 如果科尔尼洛夫叛乱取得成功, 并且叛军顺利开进彼得格勒, 那么, 克伦斯基的命运将会变得十分悲惨。科尔尼洛夫将军就像克伦斯基喉咙里的一根刺。克伦斯基原本希望科尔尼洛夫率领他的“野蛮师”进驻彼得格勒, 维护首都“秩序”, 但他明白, 这同时又将是他个人手中权力的终结。
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彼此之间的敌意难以掩饰。科尔尼洛夫大骂临时政府成员是“俄国的走狗”, 他是这样评论克伦斯基其人其事的:“我必须告诉你的是, 我再也不会相信什么克伦斯基和临时政府。临时政府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让我们依靠强权, 也就是只依靠一个强势的政府就足以挽救祖国。至于谈到克伦斯基, 他不仅软弱无能, 犹疑不决, 而且还缺乏真诚。”[5](p.218)然而, 克伦斯基却是这样如实地描述科尔尼洛夫的:“就连最聪明的人都不能破解科尔尼洛夫的神秘举止。”[5](p.221)
当时, 授命陆军部长А.И.韦尔霍夫斯基接替科尔尼洛夫的职位, 这个任命就像克伦斯基所写, 让人们觉得过于“科尔尼洛夫化”。对此, 克伦斯基指出:“此外, 由于其他候选人的行为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我本义上没有任何可选择的人选。当时, 无论是左派, 还是右派, 都表达了各自愿望, 希望陆军部长接替科尔尼洛夫。”[5](p.223)
“科尔尼洛夫叛乱”发生后, 克伦斯基在军中失去了全部支持力量, 但却得到来自军队底层的“支持”, 布尔什维克在当中享有深厚的威望。因此, 克伦斯基已经不能公开地中伤布尔什维克:革命群众站在布尔什维克一方, 正是他们使克伦斯基摆脱了科尔尼洛夫危机。克伦斯基自己也不清楚, 谁才是他最害怕的人:“尽管科尔尼洛夫的冒进行为遭到挫败, 但这种冒险给俄国带来厄运, 因此深刻痛苦地打击人民群众的意识。这一次的叛乱造成了更大的动荡, 后果是意想不到的。一小撮分子的冒险行为转变成整个资产阶级及社会上层反民主、反工人群众的政治阴谋。到8月13日, 布尔什维克对局势表现得无能为力, 手足无措。但9月7日, 布尔什维克成为彼得格勒工人士兵代表委员会的领导, 在整个革命阶段, 大部分布尔什维克深得民心, 他们赢得了革命的胜利。”[5](pp.17-18)克伦斯基在其他地方发现:“科尔尼洛夫冒险行为成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前奏。如果没有9月9日, 就没有11月7日。”[5](p.277)
克伦斯基将科尔尼洛夫叛乱定义为“冒险”, 将十月革命称作“变革”。克伦斯基的头脑足够清醒, 他明白, 在极其复杂的形势下, 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已成为不可避免。“社会主义分子”克伦斯基清楚这一点, 布尔什维克的列宁同样也不例外。列宁随后说道:“10月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恰好对群众的力量做出了准确的估计。我们不仅认为, 而且根据群众选举苏维埃的经验切实地知道:9月和10月初绝大多数工人和士兵已经转到我们方面来了。我们单从民主会议的表决情况也可以看出:即使在农民中, 联合也破产了, 就是说, 我们的事业已经赢得了胜利。”[8](p.360)10月已经来临!我们始终坚信,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时机将要到来!但是, 经过政权由临时政府逐渐过渡到苏维埃这一时期后, 克伦斯基的政治生涯只能画上了句号。
克伦斯基指出, 的确有这样的事实存在:“由于战事不利, 军权掌控在平定9月科尔尼洛夫叛乱的领导人手中, 军队充满了反临时政府的情绪。”[5](p.207)结果, 布尔什维克将军队掌握在手中。在这种形势下, 布尔什维克担当起夺取政权的重任。关于这一点, 列宁在9月12—14日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 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的信中写道:“布尔什维克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之后, 可以而且应当夺取国家政权。”[10](p.232)列宁用到“应当”这个词语, 因为在这种条件下, 拒绝夺权就意味着将政权自愿归还反动将领们的手中。
克伦斯基试图站在一个既能安抚右派, 又能体恤左派的立场上。但恰恰因为这一点, 他最后落个敌我不分的下场。克伦斯基抱怨说:“我很难做人, 因为我同左派布尔什维克和右派布尔什维克同时斗争。我想走中间路线, 可是那样就不再会有人帮我。”[11](p.54)但是, 正如一位经典作家揭示的, 最卑鄙的政党就是中立的政党, “走中间路线必遭失败”。
顺便说一句, 临时政府许诺9月17日召开立宪会议, 但情况发生了变化, 无论是9月, 还是10月都不能举行立宪会议, 到1918年1月, 为解决和平与土地问题, 才召开了立宪会议, 但1917年10月26日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已解决了和平与土地问题。
“向冬宫发起猛攻”和召开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被视为是革命最高峰时期。《20世纪的俄国史》教科书的作者这样写道:“十月革命 (10月24—25日) 踏着胜利的节奏取得了彼得格勒胜利。”[1](p.17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布) 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一位军事领导, 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А.Ф.伊林—热尼瓦对当时形势做了如下描述:“只有为数不多的一小撮贵族士官生响应临时政府号召……显然, 整个彼得格勒警备部队站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一方……我编制了一幅关于赶到冬宫支援临时政府的军队数量的统计图:
米哈伊洛夫斯克军事学校的两个分校;彼得霍夫陆军准尉军校士官生700人;奥拉宁鲍姆陆军准尉军校士官生300人;加契纳陆军准尉军校士官生三个连 (约500人) ;女子突击队200人;哥萨克200人。总计约2 000人……继续等待已经十分可笑, 因此, 彼得格勒苏维埃决定向冬宫进攻, 推翻临时政府并夺取政权。”[12](p.226)
派去侦察的士兵汇报说:“一切进展顺利, 冬宫守卫部队已经投降”, 女子突击队也“投降”了[12](p.226)。
等待很可笑, “更可笑的”是普列汉诺夫的立场暴露得一清二楚, 当彼得格勒苏维埃夺取政权后, 普列汉诺夫写给彼得格勒工人一封公开信中谈到, 工人们夺取政权徒劳无益!但是, 为什么不夺取呢?如果政权自己倾向于你这一方, 受你掌控的话?布尔什维克“注定”会夺取政权。就连克伦斯基本人也十分清楚自己的宿命何在。起义队伍实际上已经掌握了政权, 接下来只涉及转交形式的问题, 1917年10月25日夜到26日完成政权的交接仪式。如果临时政府向广播电台发出最后通牒, 并向冬宫守卫部队发布命令停止任何抵抗的话, 整个交接过程就不会有流血事件发生, 但几乎没有发生这一切情况。
如果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们听从了孟什维克一位领袖Ю.О.马尔托夫的号召, 那么流血还会更多、更加严重。目击者关于这一切写道:“马尔托夫用歇斯底里的沙哑的嗓音开始千方百计地辱骂布尔什维克, 将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称为‘政治阴谋’, 他建议起义工人和士兵明白事理, 保持冷静, 现在醒悟还为时不晚。他号召代表们走上彼得格勒街头, 劝说起义队伍解散各自回家。”[12](p.313)
孟什维克遭到挫败并离开了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孟什维克Н.Н.苏哈诺夫在自己的《革命回忆录》里写道:“我们离开了, 不知道要去何方, 也不知道为什么, 同苏维埃决裂后, 将自己同反革命分子混在一起, 破坏和贬低了自己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 自己组织和原则的全部未来被捣毁。这些还不够, 我们的离开使布尔什维克完全放手去展开革命行动, 在我们将自己的革命舞台完全退让给他们之后, 使他们变成整个社会阶层具有完全意义的公民。”[13](p.343)
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没有意识到, 事态不可能“和平”结束。如果起义队伍被说服并各自解散回家的话, 那么, 加契纳城下的П.Н.克拉斯诺夫将军会迅速到达圣彼得堡以维持“秩序”, 其结果是血染涅瓦河, 以及北巴尔米拉运河。有位当代人说得对:如果打仗不可避免, 那么就要先发制人, 出奇制胜。
按照列宁的话说, 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无论如何都没有上升到“革命辩证法”这一认识高度, 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临时政府的捍卫者实际上只有那些士官学校的学生, 这些士官生先是被捕, 当他们承诺再也不会参与这个事件之后被释放回家。
随着形势明朗起来, 先是人民, 之后包括军队在内都没有站在临时政府一方。一般认为, 进攻冬宫人员阵亡6人, 一切证明并没有发生军事政变, 这只是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
十月后的革命
如前所说, 苏维埃夺取政权只是一种纯粹形式上的行为, 因为人民已经不再倒向临时政府一方, 但军队还是勉强地坚持战斗在反德前方战线。克伦斯基租赁美国大使的一辆汽车 (甚至都没找到自己的汽车) 去迎接他期待的援军的到来。至于伪装穿上裙子, 那当然是一种情感的渲染和夸张, 但克伦斯基还是乔装打扮了一番:“有人建议我换上水手服, 水兵帽, 带上汽车司机的眼镜。水兵服太短, 水兵帽太小, 勉强地带在头顶。我认为, 这种情形就像化装舞会一样荒谬怪诞, 过于危险, 但也出于无奈。我只上演了几分钟的时间。”[4](p.362)
这一切都发生在已经由革命的士兵和水手控制下的加契纳。克伦斯基和他的随从被困在加契纳宫。1927年, 克伦斯基写道:“甚至无法阻止的巨大的危险都难以促使我们团结起来……哥萨克不断地怒骂官兵, 令其去遭受不可避免的死亡。官兵遭遇了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士兵和哥萨克的猛烈进攻……试想, 如果布尔什维克夺取加契纳, 那么, 为挽救个人生命又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当看见增援部队延迟到来的时候, 哥萨克真诚相信了出卖背叛他们的是什么。军官们没有看出有什么必要去隐瞒对我的憎恨, 我感受到自己已经没有力量保护他们, 人们的愤怒不可避免。”[4](pp.358-359)
11月14日早, П.Е.德边科领导的水兵代表团到达谈判地点。“水兵要求克伦斯基无条件释放布尔什维克, 哥萨克准备接受这一请求”[4](p.359)。他们同意:“哥萨克用牺牲一个人性命为代价, 购买手持武器返回家乡的自由与权利。”[4](p.361)就像克伦斯基所写的, 当时出现了“两个我不认识的人, 一个士兵, 一个水兵”, 这两个人建议他换掉衣服, 乔装打扮。克伦斯基原本从水兵那里跑掉, 现在水兵又在解救他。这一点表明, 整个革命重要的决定性人物就是革命的水兵, 而不是那些将军, 更不是海军上将高尔察克。
克伦斯基从加契纳逃向森林, 但这并不是革命的终结。列宁非常清楚, 十月革命的胜利不是最后的也不是完全彻底的胜利。主要的是, “世界革命”能否支持俄国的革命, “世界革命”发展明显处于迟滞阶段。同样, 俄国革命也没有在10月结束。还剩下一个可能的权力中心, 即临时政府无论如何都没能解散的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召开了立宪会议, 而从5日夜到翌日凌晨5点, 会议终止。
布尔什维克被控诉“驱散”了立宪会议。对此, 列宁有针对性地发出了指示:“在得知海军人民委员德边科下令驱赶反动的立宪会议代表后, 指示德边科和塔夫利达宫警卫队长A.Г.热列兹尼亚科夫:对反动的立宪会议代表不得使用暴力, 可以放行, 但是, 不准许随便进入塔夫利达宫。”[8](p.597)
立宪会议内部隐藏有反动代表。如果革命允许身边有反革命分子出现, 那会是多么奇怪的事情。1月5日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宣读了立宪会议党团声明, 其中建议立宪会议承认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政权, 还宣读了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法令。立宪会议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并不认同这一切, 之后, 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离开了会议。
布尔什维克通过的声明中谈道:“我们一分钟也不愿意掩饰人民公敌的罪行, 我们声明退出立宪会议, 以便把怎样对待反革命的那部分立宪会议代表问题提交苏维埃政权做最后决定。”[8](p.235)声明还说:“目前这种成分的立宪会议, 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前形成的力量对比的结果。现在立宪会议中的反革命多数是按照过了时的政党候选人名单选出的, 它代表革命的昨天, 它企图阻挡工农运动的道路。”[8](p.234)
选举后俄国社会革命党分裂为左派和右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担任政府成员, 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转向加入了反革命阵营。如果立宪会议仍然是它召集开会时的那些代表的话, 那么, 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离开后, 实质上, 形势又恢复到十月革命前两个政权并存的时期。因此, 1月3日 (16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绝非偶然, 其中谈道:“任何人和任何机关攫取国家政权某种职能的任何尝试, 都应视为反革命行动。任何这类尝试, 苏维埃政权都将使用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予以镇压, 直至使用武力。”[8](p.233)
解散立宪会议后, 政权最终转归苏维埃。列宁说:“人民要求召集立宪会议, 于是我们召集了立宪会议。但是, 人民立刻就感觉到这个名声显赫的立宪会议究竟是怎么回事了。现在我们执行了人民的意志, 人民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8](p.245)
解散的立宪会议的“民主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将活动中心移到萨马拉, 在那里成立了全俄立宪会议委员会 (КОМУЧ) 。就像克伦斯基在1917年10—11月的情况, 立宪会议试图躲藏在白军羽翼下寻求保护。逃亡到“鄂木斯克地方政府”的立宪会议委员会成员被1918年12月鄂木斯克工人武装起义官兵枪决。
我们看看苏联军事史学家Н.Е.卡库林对这些事件的描述:“切尔诺夫和其他几位立宪会议代表被捕。切尔诺夫很快得到捷克斯洛伐克兵团的释放:他同其他几个人成功逃跑, 苏维埃政府对他们实行宽大政策, 但很快这些人就发动了新一轮政治阴谋以此回报苏维埃政府。其他被捕人员和押送到鄂木斯克的立宪会议代表遭遇到更加悲惨的命运:被关进鄂木斯克监狱, 在那里, 当1918年冬天鄂木斯克工人举行起义时, 被部队军官擅自执行枪决。”[14](pp.58-59)
各地区诞生了相当多的“民主”政府, 他们的总体命运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这些政府要么被白军将领歼灭, 特别是杜托夫、卡尔梅克夫、谢苗诺夫之流的白军首领;要么他们成为叛军独裁政权的挡箭牌。这些白军将领们清楚, 他们应该装装样子, 看上去哪怕有那么一点点“民主派”的样子呢。
海军上将高尔察克被宣布是“俄国最高执政者”。1918年11月28日, 高尔察克对媒体代表声明:“只有奠定在稳固的民主主义基础上, 我们今天的国家才能够存活和发展下去。”[14](p.59)显然, 今天的“民主派”将高尔察克上将塑造成一位不知畏惧和从无抱怨的、难得的英雄豪杰形象。但是, 在“民主派”的防护罩下, 他都干了些什么呢?他的反动政府的行政管理人员写道:“其行为已严重违法, 未经法庭判决就实施酷刑镇压, 甚至鞭笞妇女, 对‘逃跑’的囚犯处以死刑, 根据密报大肆展开拘捕行动, 将民事纠纷转交军事当局处理, 凭着诽谤、诬陷和阴谋诡计实施非法追捕, 当这一切严重影响到普通公民生活的时候, 这位统帅却只能是事件的见证人。除此之外, 我不清楚, 难道就没有哪一件事情能够追究这位本已罪行累累的军事统帅的责任?为什么又仅凭一条谗言诽谤就能将遵纪守法的公民关押入狱?”[14](p.61)
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的军事独裁政权主要的社会基础只能是西伯利亚农民, 但他却派出讨伐队去征讨这些农民:“农民遭到鞭打, 掠夺, 他们的尊严被侮辱, 破产。上百名遭惩治受屈辱的人中, 可能也就有一位是真正犯了罪的。”[14](p.61)
鞭笞是俄国“民主”政权最通行的万能的惩治方法, 一个很有趣的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监禁被指定在白军头目谢苗诺夫的军列指挥部里:“不说报告二字就不能擅自闯入, 否则就鞭笞他。”结果, 所有人, 老人、妇女和儿童及其他人都遭到这样的刑法。“全城不断发生社会主义民主派代表和知识分子毒刑拷打事件, 例如, 一位参加11月18日谈判的代表就被悬挂在坎斯克城市广场上”[14](p.61)。
邓尼金的所作所为丝毫不逊色于高尔察克。卡库林援引Г.К.金斯的话说:“酒鬼, 鞭笞毒打, 屠杀和劫掠反倒成为日常现象。”[14](p.78)邓尼金反动政府著名的活动家К.Н.索科洛夫写道:“畅通无阻地有计划地劫掠居民已是一种规则, 各级军官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都参与了这一暴行。”[14](p.78)
尤登尼奇发生了什么事情?从红军临阵逃脱的布拉克—巴拉霍维奇负责管理尤登尼奇的这些军政事务。卡库林这里援引了М.С.马尔古利斯的一篇文章《武装干涉的第一年》:“将人白天悬挂在市中心的灯笼杆上, 并且, 巴拉霍维奇的副官建议被处以死刑的人自缢。一排排悬挂着死人尸首的木杆装点着全城的街道, 有些地方甚至是每根木杆上悬挂着三个人。最终, 俄国的同盟军代表发动起义反对城里白军的暴行, 于是, 巴拉霍维奇将自己的行刑地点移到城郊。”[14](p.81)
白匪对反对自己的农民施行残酷镇压, 而农民却是其统治的社会基础。Н.马赫诺就是这样使“志愿军”的大后方遭受重创。红军在那里不必费一兵一卒, 因为“志愿军”必然自行灭亡。高尔察克的统治遭受了同样命运, 他的军队在红军还未到达前就已经被当地的西伯利亚人歼灭。卡库林写道:“内战最主要的推动力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农民。农民阶层是摇摆不定的元素, 总是从一方抛到另一方, 总之, 成为力量双方最终抗衡的决定性因素。”[14](p.46)白军将领及其“政权”采用的残酷镇压手段将农民阶层推向革命一方。
跑到克里米亚投奔弗兰格尔政权任职服役的“民主主义者”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П.Б.司徒卢威亲眼所见, 弗兰格尔将军在自己的“功勋簿”上书写的都是什么内容:“我决定做一项实验, 用我们抓来的俘虏去补充哥萨克特种步兵。根据出身, 将各级指挥人员, 直到班长全部挑选出来, 包括370人, 我命令立即对他们执行枪决。然后, 我向余下的人宣布, 他们应为这样的命运安排感到自豪, 值得参加这场实验。我将责任转嫁给那些领导他们反对自己祖国的人身上, 我想给他们一个赎罪的机会, 并证明他们都是对祖国心怀忠诚的儿子。”[15](pp.104-105)
370条人命!就这么白白葬送了, 就像一件平常事一样!今天崇尚屠杀俄罗斯人民的那些败类仍然认为:有什么办法, 战争就是战争。但战争是双方的行为, 为什么在那个年代就要揭发红军对白军的“暴行”呢, 他们哪怕列举出数百名普通俄国人被射杀一个事件也足以说明问题了。克里米亚“疲惫的太阳”号轮船记住了所发生的一切, 弗兰格尔男爵逃离克里米亚, 限于轮船空间有限, 他抛弃了自己手下的军官, 使其听凭命运摆布。
经历了这一切, 我们坚信, “布尔什维克”要用武力夺取政权!关于“布尔什维克”, 我们不得不有条件地说, 因为从1920年年初, 伊尔库茨克政权已成为“政治中心”, 该中心主要由社会革命党人组成, 他们把高尔察克交给法庭。高尔察克的罪过主要是, 他纵容杀害立宪会议代表, 以及自己政敌的犯罪行为。没等到布尔什维克到来, 高尔察克就被执行了枪决。
小结
克伦斯基谈到“民主政治”, 并将“民主政治”与“布尔什维克”相对立, 但是谁也不需要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问题明摆着:要么实行反动将领的军事独裁政权, 要么“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孟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客观地站在反革命立场上, 普列汉诺夫正是在这时候与“马克思主义者”挥手告别。
列宁从1917年4月开始, 已经不再称他为“同志”, 而是改称“先生”, 这其中不无原因。“我们很容易地战胜了我国的卡列金分子, 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 而只遇到一些甚至不值得过多注意的反抗, 那是因为事件的这一进程已经由以往的整个客观, 发展预先决定好了, 我们只要最后说一句话, 换一块招牌, 把‘苏维埃是工会组织’的字样擦掉, 写上‘苏维埃是唯一的国家政权形式’就行了。可是在组织任务方面,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9](p.5)。
签订布列斯特条约面向的未来道路十分艰难。苏维埃开始将私人不动产转归国有, 将土地分配给农民, 对工业加强人民监督管理。实质上, 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相符合, 但是, 一切情形都是公开化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单独论述。
参考文献
[1]А.Н.Боханов, М.М.Горинов, В.П.Дмитренко и др.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XX века, Москва: ACT, 1998.
[2]列宁全集: 第 29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4]А.Ф.Керенский.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1917, Москва: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05.
[5]А.Ф.Керенский.Прелюдия к большевизму, Москва: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06.
[6]А.П.Ненароков.1917.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документы, фотографии,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7.
[7]Р.А.Белоусов.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а: в 4кн.Книга первая: На рубеже двухстолетий, Москва:ИздАТ, 1999.
[8]列宁全集: 第 33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9]列宁全集: 第 34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10]列宁全集: 第 32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11]В.Б.Перхавко ( составитель)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юного историк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Москва:Педагогика-Пресс, 1998.
[12]К.В.Гусев, П.А.Голуб, В.И.Миллер, Т.Ф.Кузьмин.Серия《История КПСС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в 2 кн., Это есть наш последний и решительный бой! : Кн.2.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7.
[13]Н.Н.Суханов.Записки о революции: в 3 т.Москва:Республика, 1992.Т.3.
[14]Н.Е.Какурин.Как сражалась революция: в 2 т.Т.1: 1917-1918 гг.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0.
[15]П.Н.Врангели.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Москва: Центрполиграф, 2006.
(作者单位:莫斯科别洛乌索沃国际高等商业学院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译者单位: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 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来源:《北方论丛 》201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