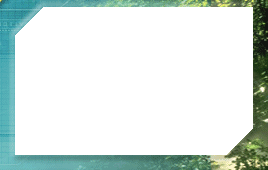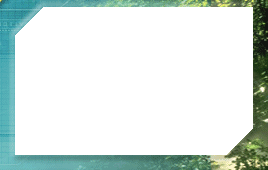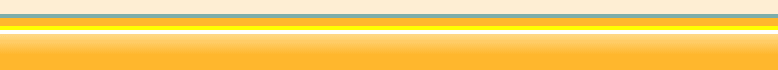资本过剩是明显的,但农业领域中的过剩从没有被真正承认过,这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
一、农业生产过剩
资本过剩是明显的,但农业领域中的过剩从没有被真正承认过,这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
《中国经营报》:你一直关注农村建设,但有些学者认为,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生活的消失是社会现代化进程当中的一个必然,你怎么看?
温铁军:国际上也有过很多关于“终结农民”的所谓学术讨论,我历来没有对这些说法表示过认可,是因为它本源于以殖民化为条件的大生产理论。而所谓大生产理论,又恰是上世纪30年代美苏两个政治对立的体系在经济领域最为一致的表达——在美国是福特主义,在前苏联则是斯大林主义——纯粹从经济上看这两者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这种话语的表达方式稍有不同,其“后殖民主义”内涵却何其相似。我们应该理解这些说法的历史背景,但是恐怕也得通过媒体提醒一下,中国当前某些似是而非的说法背后,也有利益背景。这个背景多说无益,作为学者,应该把一个客观的思考端出来,任由不同利益群体或者不同利益集团做取舍。愿意舍的人他就舍,愿意取的人他就取,与我何干。当然,随着社会进步和人们认识的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仅去拷问这些人的理论,而且去拷问这些人的背景。
《中国经营报》:生态文明的提法被看做十八大报告中的一个亮点,你如何看待生态文明这个概念?
温铁军:思想理论界早就有人提出所谓工业文明时代与资本主义的终结,其实,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生态文明的提出,就已经是一个重大发展理念的调整了。什么叫生态文明?照本宣科的人试图做很多附会解释,但生态文明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内涵具有多样性并且必须尊重自然界和人类的多样性存在。具体来说,无论人类以什么方式存在,都是作为自然界一个部分维持其融入自然的生计方式。比如,人类在黄土高原本来住窑洞,那比住砖盖的房子冬暖夏凉,它的使用寿命也未必比钢筋水泥的房子短多少,为什么一定要把窑洞都拆了,把本来就冬暖夏凉的居住环境改造成一个必须用工业文明制造的空调和暖气的环境?
《中国经营报》: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障碍是什么?
温铁军:生态文明在中国的实现,可能还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因为中国追求工业文明这一百年已经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在向生态文明转型过程中这个成本如何消化,是个还没有被深刻认识的大问题。比如,今天中国农业为追求符合工业文明要求的现代化,已经使农业成了我们国家面源污染一个贡献最大的领域,大大超过了城市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为罕见的。再具体些看,自从产业资本扩张的90年代建设设施农业以来,我国大棚面积已经占全球大棚总面积的87%。哪个国家有我们这么大量超采极度稀缺地下水资源的所谓“现代化”设施农业?还有,我们占全球19%的人口,生产了全球67%的蔬菜、50.1%的猪肉、30%的大米,而这些由资深专家提供的数据解释了很多弊病——快速资本化农业长期追求粗放的数量增长,当然会导致菜贱伤农、谷贱伤农和肉价大起大落!对此,有人认真反思过吗?这样因产业资本过剩向农村转嫁成本的现代化生产,还造成了中国每年的食物浪费至少是20%以上。为什么政策专家们没有把这些数据拿来说事,这不都是随手可得的数据吗?我在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两型农业的同时就主办过国际会议,到会的国际组织提供的全世界54个国家的专家测算出的权威数据是,如果按照人均卡路里计算的满足健康生存的实际需求量,全球农业生产的总过剩是30%,世界之所以有饥饿,主要是制度不合理。
《中国经营报》:农业生产过剩的确很少听到,我们更多强调的是保证粮食安全。
温铁军:这种倒掉牛奶、埋掉果菜等教科书式的农业过剩现象已多次出现。因此,指出生产过剩不是我的发明,而是资本主义时代的ABC。马洪、陆百甫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及我们同辈的林毅夫,都先后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指出中国出现生产过剩危机。我们现在产业资本过剩是明显的,但农业领域中的过剩从没有被真正承认过,这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当然,学术界内部大家都讨论过这个产业过剩问题,认为我们现在的做法是用远期过剩掩盖当期过剩,这恐怕也是政策界的共识。这样的共识却很少出现在公共媒体上,除了媒体的失职,背后也有利益集团的急功近利在作祟。
《中国经营报》:最近讲述上世纪40年代大饥荒的电影《一九四二》正在上映,是不是国人对饥饿的集体记忆太深了,所以更强调粮食安全?
温铁军:我不能解释电影,只能说客观事实是什么,而且这都是有国内外的研究数据作为依据的。这数据也不是我发明出来的,我只不过摘引了这些数据。每年农民都被农产品价格波动折腾得死去活来,难道不是我国农业引入后殖民主义的大生产理论在半个世纪的实践中已经造成过剩的最好例证吗?
二、中国不适合产业化农业之路
如果听任资本集团推进这种大规模资本化的农业,其结果就是农业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日趋严重。
《中国经营报》:产业资本和农业生产双双过剩,而你对产业资本进入农业也一直保持很警惕的态度现在有所改变吗?
温铁军:那是因为在当年农业产业化的始作俑者中,我也是其中之一。彼时决策层要搞产业化农业。我是农业产业化政策的首批研究人员之一。但我当时就在研究报告中指出,通过拉长产业链的方式增加农业收益的政策思路符合一般经济理性,但检验农业产业化成功与否的标准不是看产业资本的收益,也不能简单看农业装备系数提高了多少,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了多少,而是要看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农民,在这个过程中的收益到底增加了多少,组织化程度提高了多少;如果农民达不到这个产业的平均收益率,那就不能认为农业产业化成功了。这是我坚持“‘三农’问题必须以农民为首”的政策思想而在9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但至今没看到任何有关产业化政策文件强调过这个检验标准。
《中国经营报》:通过引入产业资本提高农业的装备水平,走大农场的模式,你不认可这样的路径?
温铁军:我从来没有什么反对和同意,作为一个坚持客观立场的学者,应该是坚持去价值化的研究,我在其中没有任何利益,为什么要表示对错呢。我只想说,客观情况是,以现在的农业政策思路和所谓产业化农业的发展模式,造成的客观后果是:农业从提供双重正外部性的产业变成了制造污染和食品安全恶化的双重负外部性的产业。
《中国经营报》:近些年来,不断有新闻曝出大型国有企业,或者民营资本、跨国企业,进入农业领域,这个趋势似乎不可逆转?
温铁军:这个问题大概在1996年前后就被提出了。当时是三九集团牵头28家大型工商企业提出推进农业产业化的人大提案。这个提案是农业部转到我们手里,由我处理、回复的。从那时开始,工商业资本促进农业产业化就破题了。可以说,现在这些企业进入农业和十五六年前的那些提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一般而言,资本化农业一定必须靠土地和其他资源的规模化,通过占有更大规模的绝对地租,来支付提高农业的装备系数、提高设施化农业水平的巨大成本。但是,从国际经验来看,只有美加澳这些殖民地国家才有大农业模式,主要是通过外来殖民者大规模占有原住民土地,才能形成绝对地租的总量增加,由此来对冲掉资本化过程中的投入成本。如果你真的想强调生态文明,就应该知道,把上万头牛集中到一起打隔、放屁所造成的甲烷污染比汽车尾气的污染要严重得多。但我们目前农业领域中的决策者仍然坚持这样高污染的道路,这是值得社会反思的。当然,这算是带有价值判断了。我只想告诉大家,在中国这样100%的原住民国家本来就人口众多,并且农业已经造成严重面源污染的情况下,如果听任资本集团推进这种大规模资本化的农业,其结果就是农业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日趋严重。
三、城市化之辩
别说我危言耸听,现在城市出现这么多群体性事件,不是已经足够警醒了吗?
《中国经营报》:你对城市化也一直持否定态度,认为那只是一个梦想。现在随着经济增长压力的加大,很多学者还是会把城市化作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主要支撑,你的观点是否有变化?
温铁军:不是观点变化,而是不断调研和反思,提高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通过长期的国际比较研究,我提出过一个基本判断,在大型发展中国家中我的确没有看到城市化成功的典范。如果有谁看到了请告诉我,我会去虚心学习。有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很高,比如巴西、委内瑞拉等国家,但都出现了“空间平移集中贫困”的规律性现象,也即大量出现贫民窟。那是社会的灰色地带,黑势力滋生,黄赌毒泛滥,正规的国家制度难以有效执行,所以才有巴西出动国防军去打黑社会,墨西哥正规的警察无法抗衡毒贩的现象。中国到目前为止已经通过诸如西部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一系列的国家大规模投资,相对地解决了原来的“准贫民窟”问题。现在我们的城市化率尽管达到了51%左右,但其实仍然有数以亿计的人处于城市边缘的“蚁族”状态,决策者稍有不慎,他们就会变成贫民窟化的灰色生存。
在中国,农民进城要考虑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现在农民工按照国家要求上四险的比例不到20%,为什么?因为现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的成本低于城市,打工者一般不需要在城里再建另外一套自己额外交钱的保障,更何况城乡二元分割,农村的保障带不进城市,城市的保障带不回农村,这就客观导致各地政府让进城打工者缴纳社会保险是加重他们的负担、本地财政占便宜。二是农民进城前后的身份变化。在农村,农民有房子有地,相当于“小资产阶级”,你让他变成产业工人,意味着变成无产阶级,有人愿意从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吗?改革开放前,农民没有地、仅有房子,城市工人却生老病死有依靠,工农之间的差别相当于中产阶级跟贫民的差别,所以农村才会出现一人当工人,全家都幸福的情况。现在还是这样吗?我不反对城市化,只是提醒政策制定者要多做实际调研,别拍脑袋下结论。
《中国经营报》:但中国的城乡二元的结构,最终是要通过城市化进程来解决吧?
温铁军:其实那也是反生态文明的观点,经过这十多年的国际比较研究,我们的意见也都向上反映了。现在看来决策层应该是听进去了,他们强调中国要加快城市化,但我们的城市化是要通过城镇化来实现的,在“十一五”规划谈到新农村建设的部分,重点强调了县域经济发展,那要依托于两大内容——中小企业发展和城镇化。这个政策思想跟一般意义上的加快城市化是不同的。更进一步从理论上讲,城市化其实是一个资本集中和风险同步集中的过程。城里人现在享受的是资本的溢出效应,但同时能不能有效地把城市化的风险弱化掉,就要考验政策艺术或治理能力了。
我在刚出版的《八次危机》中提出,以往遭遇的八次社会经济危机凡属于能够向农村转嫁成本的就都实现了软着陆,凡属于不能向农村转嫁成本的就会硬着陆。当我们把农村彻底“化”掉的时候,危机实现软着陆的条件就没有了,而硬着陆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一定会引发社会政治动乱。别说我危言耸听,现在城市出现这么多群体性事件,不是已经足够警醒了吗?是想让内部矛盾分散化,还是想让矛盾集中起来爆发,这是牵扯到能否和谐稳定的大问题。决策者千万别被少数利益集团左右,因为城市化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资本、特别是房地产资本和金融资本相结合的资本扩张,意味着这些利益集团攫取更大规模的利益。
来源:《中国经营报》2017年7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