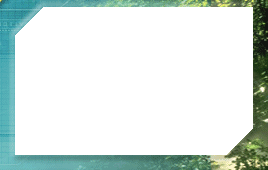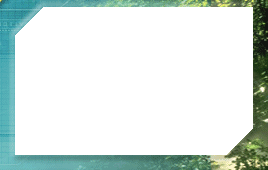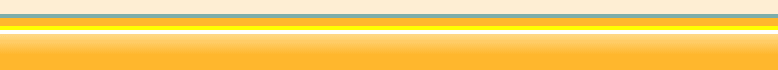张亚斌
那一年,十八岁的我,考上了北京一所大学。很自然,这就决定了我,将开始有生以来的一次极不平凡的旅行。
时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已经到了八月底,由于雨季的提前到来,我这个从未出过家门的孩子就过早地陷入对旅途的忧虑之中。是啊,那时,我一面沉湎于考上大学的喜悦里;另一方面,又为自己从未出过远门而不安,我实在无法想象那个千里迢迢的旅途中等待我的是什么?
秋雨淅淅沥沥的下着,我的心理随之瞀乱不已……。
干大告诉我,北京很远很远,得从省城坐一天一夜火车。他还说,出门在外,孤身一人,最要紧的是看好自己的行李,尤其是坐火车时,行李必须放在自己座位对面的行李架上,以便自己随时能够看得见。他还反复叮咛我,火车进站前,千万不要上厕所,不然,自己的行李被人拿走,自己竟还不知道。最后,他还谆谆告诫我:好哇哩,社会太复杂啦,可要小心谨慎哪!……。
干大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见过世面的人之一,他的话,对我来讲,显得格外珍重。不过,他的话,着实也吓得我够呛,以至本就心惊胆颤的我,听完他的教诲,就更加胆怯、害怕了,并对自己的旅途,充满了忧虑。对于遥远旅途的恐惧,犹如对于遥远都市的憧憬一样,搅得我那几日心神不定,彻夜难眠……。
临走的那天晚上,村里人纷纷涌进我家,他们拿着鸡蛋、粮票等东西为我送行。我默默地注视着这些纯朴、善良的人们,仔细倾听他们语重心长的忠告,听着他们热烈激动地谈论,我的心理骤然生出无限的暖意。是啊!这些看着我长大的乡亲们,他们给予我多们深情的厚望呀,可不是么,当他们得知我是方圆数十里唯一考上北京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甭提他们心里有多自豪和激动啊,毕竟我是他们的骄傲啊。
那天晚上,乡亲们走得很晚很晚,当他们意犹未尽地走出我家大门的时候,我体会到一种纯朴的情感叫感动。
夜深了,姐姐们还在为我整衣服,烙干粮,收拾行装……。噪杂忙乱的夜晚里,我在家里的土炕上,熬过了人生最难熬的漫长的一夜。整个晚上,我恍恍惚惚,睡得极不踏实,烙感觉到夜没有尽头。
第二天一大早,朦朦胧胧的黎明中,我起了床。家人们已早早起来,吃过母亲为我做的鸡蛋拌汤,我发现,本家兄弟学娃已经讨好驴车,他正和父亲将我的行李——一个大木箱、两个小包袱,一件件放进啦啦车的车厢里,并在上边结结实实地蒙上了一层油布。
阴沉的天空中,稀稀落落下起了小雨,学娃和父亲干得更起劲了,尤其是父亲,他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好像他的脚步也较往日轻松了许多:是啊!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他,此刻一定是着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已经到了分别的时刻,家里人送我穿过阒无一人的小巷,村里人此刻都还沉浸在甜蜜的梦里。我们来到了村口,黑魆魆的原野,已经渐渐显露出它的庐山真面目,若是平日,此刻东方早该发亮啦,可今天是雨天,因此,天色依然在黑暗之中挣扎着。
我和家人依依话别,千言万语,最后只凝结为两个字——“保重”,望着母亲,望着姐姐们,望着弟弟,望着他们背后那生我养我的村庄,我眼轮不由得一热,一滴滚烫的泪珠悄然滑落在我冰冷的脸面上,一种说不出的眷恋情感,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扉,甚至还刺痛了我的眼睑。我感到自己的脚步似有千斤万斤重,那是多么沉重的脚步啊,我几步一回头,不听地返身向他们挥手……。
天,越来越阴沉;雨,也越来越大。那雨滴,唰唰唰,强有力地、有节奏地抽击着我脚下的黄土小道,不一会儿,我的脚下就是一片泥泞了,似乎它们也恋恋不舍,不愿与我就此离别,它们一次又一次拉扯着我的脚步,甚至好几次都快把我的鞋要搦进去了,它们,似要留住我的脚步呀。
我,父亲,学娃冒雨向西走去,上了西岭,我最后一次回身东望,依稀看见母亲、姐姐、弟弟还在村口,不停地向我招手,我身不由己,再一次举起右臂,挥呀,挥呀,挥个不停……。
也就在那一天,在沟西,我搭上了去省城的火车,那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坐火车。滂沱的大雨中,列车冲开雨幕,在广阔的渭北平原上疾驰着,雾霭中的村庄,洗礼中的远方的白杨,似乎它们都在为我送行,我目视着它们,不由得涌起一种对这土地的深沉挚爱之情。
列车徐徐驶进西安车站。烟雨之中的古城墙,使我对这座历史文化古城,不由得产生出无穷的遐想。解放路上,潮水一般的人群,使我这个来自田野的乡下孩子,感到无比地震惊:这就是城市,这就是我一直神往的大都会,它的宏伟,它的热闹,它的新奇,使我感到格外地兴奋。
我和接我的干大跨上了一辆电车,街道两旁的商店,如万花筒一样徐徐向后转去。
那天晚上,我躺在东大街西北旅社干大唱起包租的客房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次日清晨,干大送我踏上了进京列车。这趟车,与我先天坐过的区间慢车,景象截然不同,车内非常的干净整洁,旅客们衣着各异,语言南腔北调,还有列车员自我介绍,为大家热情周到地进行送水服务。列车开始启动,我和车上那些告别的旅客一样,向阳台招手,站在那里的干大,边挥手,好像还边喊着什么。我使劲地摆了摆手,示意他赶快回去。转瞬间,干大就和站台消失了。
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旅行跋涉,列车出潼关,过洛阳,经郑州,越邯郸,穿过石家庄,终于抵达北京。次日凌晨四点,我神情疲惫地走出北京站。
空荡荡的车站广场,我找到了我那所大学的接待站,由于时间太早,那里只留下一个站牌,一张桌子。
我漫无目的,径自向广场东侧走去,见那边有一个水泥平台,于是就拿挎包当枕头,在上边睡了起来,待我醒来,发现天色已经大亮,接待站那边已经有人活动。
我平静地走过去。就在快到接待站的那一瞬间,我心想:我的新生活就随着这第一次远行开始了。
1986年9月于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