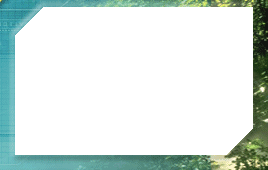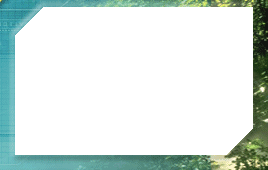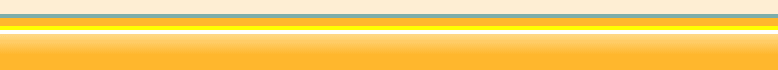一 、
近年来,“红色经典”的悄然回归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所谓“红色经典”,一般指的是一批产生于革命年代的文学作品,以“三红一创”(《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以及《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山乡巨变》、《林海雪原》、《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欧阳海之歌》等长篇小说为代表。这些作品,以记录革命战争历史和农村土地改革与合作化运动为题材,以讴歌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旋律,曾经风靡于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鼓舞了整整两代人的革命热情。而在那个暴风骤雨的年代已经烟消云散以后,在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产生的世俗化浪潮高涨的今天,“红色经典”的悄然回归又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也许是因为一批弘扬“主旋律”的影视作品的热播(例如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产生的“轰动效应”)唤起了出版商的历史记忆,使他们推出了那些“红色经典”。而“红色经典”出版以后在舆论界引起的热烈反响又促成了一批根据那些“红色经典”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的热播(例如电视剧《红旗谱》、《林海雪原》、《沙家浜》相当不错的收视率)。就这样,在影视人和出版商的互动下,“红色经典”再度走红。虽然在文化格局已经多元化的今天,“红色经典”的再度走红也很难重现当年大红大紫、洛阳纸贵的盛况,但不管怎么说,它能够重返当代人的文化生活,本身就耐人寻味。
也许是因为今天的人们多元化的精神需求使然:在看多了“清宫戏”、“反贪戏”、“警匪片”、“生活片”、“爱情片”和“港台搞笑剧”以后,“红色经典”对革命年代的回忆一下子将一股朴实、清新、真诚、崇高的气息带回到了今天的文化生活中。值得注意的是,像《激情燃烧的岁月》和《亮剑》那样的“红色记忆”已经与革命年代的“红色经典”有了一些明显的区别:当年“红色经典”中充满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息已经悄悄被石光荣、李云龙那样富有人情味的豪放、粗犷、朴实、狡黠的农民气质取代了。具有人情味的农民英雄形象显然更能使一般观众感到亲切。而根据“红色经典”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和《沙家浜》因为过度渲染了阿庆嫂的风情(这也是一种“人情味”?)和杨子荣的情史而受到部分观众的强烈批评,又显示了“红色经典”在一代人心中的记忆之深,以及“红色经典”在他们记忆深处的神圣地位。这样的批评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今天的人们(虽然只是一部分)对于“红色经典”、对于崇高精神的忠诚。这,也是多元化思潮中相当可贵的一元啊。事实上,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仍然不乏见义勇为、急公好义的平民英雄,不乏鞠躬尽瘁的人民公仆,不乏献身事业的企业家、科学家,不乏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普通劳动者。他们都以自己的感人事业证明了崇高精神的没有过时。而那种崇高精神,其实就是一直支撑着我们民族的伟大魂魄吧!由此可见,“红色经典”的重新走红原来是有深厚的文化精神作支撑的。它们是民族精神与革命话语的成功结合。
的确,这是一个世俗化的年代,是一个商品经济大潮日益高涨的年代。但世俗化的浪潮、商品经济大潮为什么就淹没不了以“红色经典”为代表的那么一种精神?
的确,这是一个文化思潮多元化的时代,是形形色色的新思潮层出不穷、争奇斗艳的时代。可在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中,以“红色经典”为代表的“正气歌”为什么仍然能够成为相当引人注目的一元?
这样的问题,是耐人寻思的。中华民族是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虽然现在已经成功走上了复兴的康庄大道,但过去岁月里的苦难经历和奋斗壮歌,已经深深融入了民族的记忆中,并成为激励后来者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这意味着,精神是可以超越时代的。时代多变,但精神却常常岿然不变。在“红色经典”中,我们不就可以从那些革命英雄的共产主义理想中感受到古老的“大同”理想,从他们的英雄业绩中感受到先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从他们不怕牺牲的凛然正气中感受到“舍身取义”的传统气概么?的确,在“红色经典”与传统文化之间,是存在着深厚的精神联系的。而这,也是“红色经典”的精神不会过时的关键所在吧。
又何止只是我们这个民族!在美国,“美国梦”就一直是激励个人奋斗、追求成功奇迹的文化标志。在二十世纪的文化词典中,“法兰西精神”、“俄罗斯精神”、“印度精神”这样的响亮口号也屡见不鲜。由此可见,二十世纪不仅是充满了战争硝烟与革命风云、科学奇迹与经济奇迹的世纪,也是各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弘扬各自的民族文化精神、并使其汇入人类精神的海洋的百年。
所以,“红色经典”的回归并不足奇。
所以,“红色经典”的回归具有深广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就这样,“红色经典”穿越了历史的云烟,使今天这个喧哗的世俗化年代与那个热闹的革命化年代奇特地联系了起来……
我甚至觉得,在这个世纪之交,除了精神的意义之外,“红色经典”的重新回归在冥冥中还蕴涵着深长的文化意义——当“三农”问题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严重程度时,当呼唤社会公正、警惕“两极分化”的声音已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回响时,当“新左派”已经成为当代颇有影响的文化思潮时,当文学界再度高涨起了关注“底层”的创作思潮时,“红色经典”也就自然成为了这股思潮中格外引人注目的一层激浪……
二 、
每一部文学经典的产生都经过了时光的考验。“红色经典”当然也不例外。它们中的不少作品,能够在众多的同类题材作品中脱颖而出,并经由电影、戏曲、连环画的改编得到进一步的传播,经由中学课本和大学教科书的重点介绍得到全民性的普及和推广,自然就赋有了强大的文学生命力。因此,它们就自然成为了“十七年文学”中影响最大的“红色经典”。另一方面,“红色经典”中有的作品(例如《青春之歌》、《三家巷》)由于题材的特殊性,受到了过于敏感的质疑与批判,而作家也慑于政治高压的威严,不得不作出相应的修改,以尽量与那个年代的政治要求保持一致,但勉为其难的修改仍然无法遮蔽其原有的丰采。在政治高压的年代里,那些动辙“上纲上线”的批判造就了许多的冤案,设置了数不清的“禁区”,但最终只是使那些受到不公正批判的作家作品在经过了磨难以后放射出了更加夺目的光芒。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也是造就“红色经典”的原因之一。
因此,对于“红色经典”传播、修改、遭禁和解禁的研究就自然成为了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清理“红色经典”传播、修改、遭禁和解禁的历史,既有助于在回眸如烟往事中感悟文学浮沉的命运,也为还原文学现象的生动与芜杂、研究作家心态的微妙起伏、揭示文学与传播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其中,有政治风云变幻的作用,有作家在困惑、苦闷、虔诚、谨慎的情绪起伏中的彷徨心迹,还有评论家、读者、电影人、戏曲家、画家在互动中见仁见智的合力。这样,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艺术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都可以在“影响传播”这个层面上得到比较集中的生动展示。
在那个年代里,文学真正成为了全民族的事业——从政治家到老百姓,从文艺家到教育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频繁的政治运动对于文学的无情打压。那一幕集辉煌与黯淡、荣耀与耻辱、单调与喧哗、僵化与热闹的历史,可谓史无前例,也肯定不会重演了。但打着那个时代鲜明烙印的“红色经典”却能够穿越历史的云烟,在当代出版界、影视界再度红火起来,就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奇观了。
三、
想到这么一个选题,得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赵国泰先生。当他希望我组织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完成这个工程时,我也感到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在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并得到了大家的同意以后,一切都紧张而有条不紊地展开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就有了这本书。这本书就这样成为我和我的学生们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晶。为此,我也衷心地感谢我的学生们。
应该说,对于“红色经典”的研究,还远远没有结束。
例如关于中国的“红色经典”在二十世纪世界“红色经典”的阵营(至少包括苏联、东欧的“红色经典”和法国的巴比塞、马尔罗、德国的布莱希特那些具有明显左派色彩的作品)中的地位,就很值得研究。中国的“红色经典”中,受到苏联“红色经典”影响的,为数不少。但就像曾经深受俄苏文学影响的作家王蒙在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的革命文学比起苏联的革命文学来,似乎缺少了什么。“不论是赵树理还是周立波、康濯,他们总是不像苏联作家、俄罗斯作家那样抒发丰富多彩乃至神奇美妙的内心。中国作家可能写得很幽默、智慧、通俗、激烈、尤其是真实、生动、纯朴,但他们从来不像苏联作家乃至旧俄作家写得那样美,那样丰满。这也许正是苏联文学里充满了幸福、生活、光荣、爱情,而中国的文学作品里净是被骗后的觉醒、翻身后的感恩、识破奸诈与显露忠诚……的缘故吧。”“为什么我们宁爱唱苏联的歌曲——雄鹰、山楂树、蓝色的头巾、海水吻着海岸、红莓花儿、雾、夜莺、白桦、褐色的眼珠……为什么我们的歌词里没有这些?我们的歌词里如果有了这些,算不算小资产阶级情调呢?我们的歌儿为什么不能表达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内心呢?”这些问题应该说是触及了“中国革命文学与苏联革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之间的差距”这样的重要课题的。在这样的问题的后面,显然有政治的因素,又何尝没有文化方面的原因?在中国文化史上,“文以载道”的主张历来深入人心。这样的主张在充分发挥了文艺的教育功能的同时也相应弱化了文艺的审美功能,已是今天学界的一般常识。“红色经典”中存在的问题(例如“红色经典”中相当普遍存在着的主要正面人物形象普遍比较单薄,常常不如“中间人物”那么血肉丰满、性格生动)显然与这样的传统影响有关。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红色经典”的文化学、语言学、叙事学研究,等等,也有待于深入的展开。一部分作家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熟悉在他们的创作中打下了鲜明的烙印(例如《林海雪原》的作者对于《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说岳全传》的熟悉使《林海雪原》也富有了侠义文化的气息,杨子荣打虎上山那一段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著名传奇;[1]《红旗谱》的作者也谈到过他学习中国小说的传统手法,通过人物的行动和对话来塑造人物性格的体会[2]);还有,作家们成功渲染出特定的地域文化氛围的笔墨(从民俗描写到方言的运用)也使“红色经典”具有了地域文化的鲜明亮色(例如《创业史》中的关中平原气息,《红旗谱》中的燕赵民俗描写,《暴风骤雨》和《林海雪原》中的东北民风描写,《山乡巨变》中的湖南山乡氛围,等等)……这些,又都使得中国的“红色经典”与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联系在了一起,从而赋有了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并与外国的“红色经典”判然区别了开来。这样,“红色经典”的中国特色就成为了有待于进一步系统、深入展开的研究课题。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是希望这本书对于有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能够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也希望有同行对于我们研究中的不当之处,多多指教。那样,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了。
文章系《红色经典影响流变史话》前言,作者樊星,2006年11月4日写于武汉大学九区
[1] 《关于〈林海雪原〉》,《林海雪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98页。
[2] 《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作家谈创作经验》,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
|